并不喜欢这本书的译名——《最好的告别》,因为它把书中带给我的东西说“窄”了。
书的原名是《Being Mortal》,直译是“凡人”。我喜欢这个名字,虽然它可能并不讨巧市场。
“凡”意味着人世的一些平等——生老病死,吃喝拉撒,还有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生命自主权”的平等。可惜这些问题人们思考得并不多,也因此显得“不凡”。
■生命自主权
——做自己人生故事的作者
虽然作者阿图·葛文德并没刻意强调“生命自主权”的理念,但它是贯穿全书的基本精神。“自主权”是现代医学伦理四大原则之首义,是医学人文思想之基石,对于医学人文的探索,如果不能进入生命自主权的维度,就只能留于表浅,所以希望“生命自主权”是本文其他所谈问题的出发点。
一位朋友86岁的父亲查出早期癌住院,家人为治疗纠结苦恼,而老人只淡淡地说:“不放疗,不化疗,我只想早点回家安静地生活。”另一位朋友为父母选择了高档疗养院,但遭到老人拒绝,父母说:我们只想在自己家里……
儿女竭力尽孝,父母却不领情,这类事比比皆是,我们总以为那是中国特色,但阿图却告诉我们——这是世界性的难题!美国老人同样有“离开自己家的担忧”,因为“好的生活是享有最多独立性的生活。”除了家,哪里还能让人拥有最多的自主与自由呢?
但老弱者面对的悖论是:周围人最想给予他们的是“安全”,而他们自己最怕失去的是“自主权”。现实中,那种在“爱”的名义下,以“安全”为目标的“控制和反控制”的矛盾并不少见,尤其是父母和儿女。只是当子女年幼时,往往是被控制者,而当他们长大,角色又反过来了。生活中,很多看起来的善与孝,因忽略了老人的“自主权”而遭到排斥,老人们维护生活自主权的挣扎则容易被视为“顽固”。
一个失衡的问题是,虽然人们常常把老人孩子并提,但对老人的心理关注远远不及对儿童,我们常常强调孩子成长中的“独立自主”空间,但对于老人“顽固”背后的心理渴望却难以察觉。其实无论是孩子的“逆反”,还是老人的“顽固”,都是在争取他们的“自主权”。
什么是“自主”?就是“可以做我们自己人生故事的作者”。书中讲了一个美式的老年偶像的故事:83岁的哈里·杜鲁门上屋顶铲雪掉了下来,医生说他是“该死的傻瓜”,老人的回击是:“我都80岁了,我有权做我想做的事情。”
现实中,这样的故事不太可能被效仿提倡,但至少提示我们:是否可以换个角度看待生活里老人们那些“老糊涂”“老顽固”的举动,并提醒自己:老人们也许生活上需要我们帮助,但不该因此而剥夺掉他们生命的“自主权”。
■衰老
——一系列的丧失
书的副标题是: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
“衰老”这个词很老,但人类对它并没有太多的经验,它是近几十年我们遇到的新尴尬——“大多数人会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由于身体太衰老、太虚弱而无法独立生活”,也就是“活得久了,问题来了”。
之前,我以为如果拥有了优质的养老机构和经济保障,就可老而无忧。然而,阿图却告诉我们:即使在美国,“退休金并没有为有限生命最后的衰弱阶段作出安排”,他的问题也困扰着我:“我们为老做好准备了吗?”我们或许做了很多事情:政策、机构、医学、养生节目……但问题是我们却很少去想:衰老意味着什么?
“衰老是一系列的丧失”——丧失耳聪目明、健步如飞、丧失记忆,丧失社会角色……直到有一天,丧失对自己生活的掌控。而生在这个“走得太快”的时代,眼花缭乱的发展变化更在某些层面加剧着老人们的丧失感。我的父母年近八旬,尚算健康,但他们不会发微信,玩淘宝,用网银,偶然外出,站在寒风里高举手臂,却只能眼巴巴看着一辆辆被APP预约走的出租车空驶而过,无奈委屈……曾经,看到父母如此“顽固”地与时代脱节,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激励他们,甚至是教育。然而,扪心自问:这些真的只是老人们自己的问题吗?我,一个中年人,何尝不也经常感慨想跟上“时代的列车”是如此辛苦无力。
在生物学意义上,我也在下行中,和父母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距离,只是暂时还没切身体会,但阿图把我带入到他们的感受中。当看到99岁的梅克沃尔说“生活中最好的事情就是你能自己去卫生间”时,我惭愧落泪:我们貌似为老人做了很多,但压根思考的角度就是主观而自以为是的,我们很少问问他们:这是您“想要的、喜欢的、需要的吗”?
阿图很诚实,他提出问题,但没有浅薄回答,因为这些问题过于复杂纠结,有些估计穷尽人类所有智慧都难以找到完美“答案”,但他的叙述和发问至少给我一点启发:可以尝试换一种角度与父母沟通,努力去理解他们的困难与需要,开始从现实的驳杂无奈中多生发出一点温暖的理解。
■当医生成为患者
——换位后的共同决策
书的第七、八章,对我是“邂逅”。当然,它谈的是生命里的艰难。
我自己正在致力于“医患共同决策”的推动。书中,阿图介绍了“家长型”“资讯型”“解释型”三种医患沟通模式,高度评价“共同决策模式”。他对共同决策中医患关系的阐释清晰到位:医生既不是战斗中的总指挥,也不仅仅是一名技师,是站在患者立场上的咨询师和顾问,他们的角色是帮助病人确定他们想要什么。
同时,阿图也以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即使在美国,“医患共同决策”从理论到被理解,被实践,也经历了长时间的浸润。这部分论述,对我不仅有启发,更有鼓励。
很感谢阿图忍着回顾的痛苦,记录了父亲从发现疾病,到选择治疗方案,最后走向善终的过程,还原了他生命中最艰难的谈话,并总结出一系列问题:“怎么理解当前情况及其潜在后果?你有哪些恐惧,哪些希望?你愿意做哪些交易,不愿意做哪些妥协?”这些记录绝不只是展示了一个完整的医疗决策过程,而且由于阿图一家都是优秀的医生,他们在选择时的思维路径对我们极具参考意义。
当然,支撑“医患共同决策”的还有文化经济等背景。比如”患”的含义,中西方就有很大不同。书中记录的几乎都是医生与患者的直接交流,但在中国,很多时候患者在关于自己健康和生命的决策选择中却迫缺席。英国医科院院士郑家强教授曾建议从医学伦理的角度考虑医患共同决策,第一个原则就是“自主权”。
“自主权”的前提是患者知情,这是一个让很多人纠结的事情,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更提倡未雨绸缪:在老人们尚有足够判断力、表达力,问题尚未成为敏感话题的时候,和他们多一些关于生命态度的交流,尽可能对一些未来或许要面对的问题厘清,以便到了需要他人帮助选择时,亲人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尊重他们的生命“自主权”。
阿图的父亲经历一次手术风险,停止或继续手术利弊难以衡量,但阿图一家果断决策,因为之前充分的交流,“父亲已经把他的决定告诉我们了”。
当然,和老人谈疾病生死,不易。但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生老病死是凡人凡事,人不可能从不思考这些问题,只是这种交流需要智慧和勇气。一位朋友的父亲查出晚期癌,短暂困惑之后,家人决定与患者一起面对困难,并尊重了患者的选择。老人安详离开后,朋友发来信息:“我发现这一代老人家对这些事是有共识的,有时瞻前顾后、畏首畏尾、越俎代庖的,反而是我们这些子女。”
能在风轻云淡时厘清,何必等到乌云密布时迷茫?
书的结尾,阿图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作为医生,事实上,作为人类,最有意义的体验会来自于帮助他人处理医学无能为力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医学能够解决的问题。”这样的认识,有职业的些许无奈,却是“人”的升华。我曾经和朋友探讨过医者成长之路,理想的线路是:从医生精进至良医,升华到大医,修炼成“哲医”(哲学家医生)。在《最好的告别》的一书中,我看到了“哲医”的影子,如王一方老师所说:“葛文德大夫完成了一个医生最完美的精神发育。”
(安杨,作者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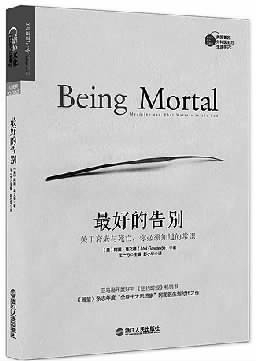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