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马一浮是20世纪的学术大家,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一生追求学术,学贯中西,涉猎广泛,在经学、史学、哲学、佛学等领域均有建树,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由于其钻研精深,行文又多微言大义,故能深入了解马一浮学术之人甚少,能集中介绍其学术之专著则更为少见。7月25日,“马一浮与国学”光明读书会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举办,读者济济一堂,听刘梦溪讲述这位“云端上的人物”。
语默动静,贞夫一也
了解马一浮不容易,因为不是简单地读他的书,就可以了解他。了解马一浮的难,在于他的学问并不都在他的著作当中。他的著述不多,我们经常读的,无非是泰和、宜山两《会语》和《复性书院讲录》,以及《尔雅台答问》和《答问补编》等。他的书信和大量诗作,是其学问的延伸,或者说是马一浮学问的另一载体,呈现的是马一浮学问境界和学术精神最生动的世界。
学术界习惯把马和熊(熊十力)、梁(梁漱溟)联系起来,称作新儒家的“三圣”。我个人认为,马先生和熊先生相比,熊先生在学理方面有一点“杂”,而且还有“理障”;而马先生不杂不泥,显微无间,毫无理障。如果把马先生和梁先生相比,梁先生未免太过讲究学问的实用性,而马先生更强调对学问本身的体验。讲经术义理,他虽然提倡践行,但绝不以通常所谓实用为依归。所以,如果以为学的本我境界来衡量,马一浮的名字在“三圣”中,应排在最前面。
马一浮与近现代以来的学术文化潮流完全不能相契,如同陈寅恪一样,也可以说是“迥异时流”。他不染尘俗,不汩习气,不沾势利。马先生是通儒,他为我们树立了一种气质清通、彻底刊落习气的纯粹学者的典范。他在纷乱的时代开启了一种文化境界,这就是不任教职、不著时文,“语默动静,贞夫一也”的境界。
马一浮是儒学大师,学术界向无异议。他的儒学研究与佛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义理学说。无论是《泰和会语》《宜山会语》,还是《复性书院讲录》,抑或是《尔雅台答问》,以及其他的文字著述,都是儒佛一体的讲述。即使是集中讲论儒学,甚至专门讲述“六艺之学”,也都是与佛学联系起来一起讲的,几乎是讲儒就讲佛,无佛不讲儒。
马一浮的治学方法,是以佛解儒,儒佛双融,儒佛会通。他的一句话说:“儒佛等是闲名,心性人所同具。”他说:“《华严》可以通《易》,《法华》可以通《诗》,苟能神会心解,得意妄言于文字之外,则义学、禅学悟道之言,亦可以与诸儒经说大义相通。”那么,马先生的学问到底哪一方面为主?我倾向是儒佛并重,儒学和佛学同为马一浮学问大厦的支柱。
马一浮向以读书多享誉士林。他的学问,是在知识的海洋中通过切身涵泳体究的结果,知识已经化作了思想,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与自性本具之义理融而为一,也就是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来源于宋代的义理之学,而又归之于先秦的“六经”,综合阐发,以佛解儒,最后形成经术义理的思想体系。因此可以说,他是少见的重视思想义理的国学学者,是20世纪一位当之无愧的思想家。
办书院,复活“六艺”之学
1938年,当马一浮在江西泰和即将转徙广西宜山之将行未离之际,他的弟子寿毅成和友人刘百闵等拟请他出山筹办一所书院之事,已经在酝酿之中了。马一浮虽应邀赴命,但系“不得已而后应”,心如静物,无减无增。
他用极短的时间起草了一份《书院之名称旨趣及简要办法》,有关书院创办的各项事宜,包括书院的性质、课程设置、讲论方法、经费来源等,均作了得其要领的叙论。他力主以“复性”二字作为书院的名称。他说:“学术人心所以分歧,皆由溺于所习而失之。复其性则同然矣。复则无妄,无妄即诚也。”
“复性书院”一名,再好不过地体现了马一浮学术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而施教的内容,则以“六艺之学”为主,究明经术义理,以期养成通儒。马一浮特别强调:“书院为纯粹研究学术团体,不涉任何政治意味。凡在院师生,不参加任何政治运动。”
马一浮深知经术义理对文化复兴可能起到的作用,他说:“窃惟国之根本,系于人心,人心之存亡,系于义理之明晦,义理之明晦,系于学术之盛衰。”这和王国维所说的“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完全是同一理据。只不过马先生认为,中国学术义理之经典道要,悉在“六经”。也可以说他是为了弘传“六经”之义理道本,养成国人健全的文化人格,为国“造士”,才不得已而有书院之举。
本来积极推动书院创办的友人刘百闵、弟子寿毅成以及教育部,都是要马一浮出任书院的院长,但马先生辞以院长之名,宁愿以“主讲”的身份主掌院务。
复性书院设在四川乐山乌尤山上的乌尤寺,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1939年农历九月十七日,书院正式开讲。马先生在《开讲日示诸生》中详阐“常”“变”之道,说中国遭夷狄侵凌是“事之至变”,力战不屈是“理之至常”;当蹇难之时有书院之设是“变”,书院讲求经术义理是“常”。
复性书院的章程由马先生亲自撰写,明文规定“求学者须遵守三戒:一不求仕宦,二不营货利,三不起斗诤”。书院之管理分任诸事项,力求简要,只设主讲一人、监院一人、都讲无定员。主讲是马先生,监院为贺昌群,乌以风为都讲。这些名称都是马先生仿古例拟定的。
复性书院自1939年下半年开讲,至1940年上半年,不到一年时间,马先生主讲的课程,已经次第展开。继前面提到的《开讲日示诸生》,续有《复性书院学规》和《读书法》两课,主要传授进学的观念和进学的方法,类似于读书为学的“发凡起例”,也可以看作是马一浮学术思想的一个纲领。
早在书院开办之前,马一浮就对丰子恺说:“书院如能完全独立,不受任何干涉,则吾亦为之。不稍假借,亦自有其立场,若有丝毫未安,决不徇人以丧己。”后来,他的立场受到了挑战,所以决定辞却主讲以实现“决不徇人以丧己”的自性目标。书院应超出现行教育体制之外,是马一浮始终不变的主张。
复性书院的创办,其由盛而衰到存而犹废到终于废置,前后十有余年。马一浮可谓甘苦自知。他实际上做了一次复活“六艺”之学的尝试,也可以看作新儒学的一次探险。好在书院于他无减无增,“十年辛苦”之后,马一浮还是马一浮。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是他的学问更入于本我之境。还有,不知他是否意识到,儒家的“六艺”之学,在20世纪的中国已经无奈而又无力。不过,马一浮本人对此并不存在“切肤之痛”,因为他本来就不曾有过奢望,“语默动静,贞夫一也”是他始终的立场。何况他的学问也从未局限于儒学一门,佛家之义学和禅学,同样是他安身立命的根基。
重新定义“国学”概念
“国学”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周礼》《汉书》《后汉书》《晋书》里面都有“国学”的概念。但中国古代历来之“国学”,指的都是国立学校的意思。南宋朱熹之前白鹿洞书院叫作白鹿洞国学,就是一所学校。那么,“国学”作为现代学术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从现有资料可见,1902年梁启超和黄遵宪的通信里开始使用“国学”的概念。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一封信里说:你提出要办《国学报》,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1902-1904年梁启超写就的《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里又使用了“国学”的概念。他说,现在有人担心“西学”这么兴旺,新学青年唾弃“国学”,很可能“国学”会走向灭亡。梁启超说不会的,“外学”越发达,“国学”反而增添活力,获得发展的生机。
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外篇”里有一节专门讲“设学”——设立学校。他说,在课程设置的时候,要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1921年梁启超写《清代学术概论》时转述了张之洞这一主张。他说,自从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梁的转述,反而成为后来思想学术的流行语。
今天研究“国学”概念的渊源与流变,可以说,张之洞在《劝学篇》里讲的“旧学”,梁启超转述的“中学”,以及梁启超与黄遵宪通信里提到的“国学”,几乎是同等概念,实际上就是中国历来的传统学问。
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1923年,北京大学的“国学门”要出版一份刊物——《国学季刊》。胡适在发刊词里讲:“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国故”是谁提出来的呢?他说,自从章太炎写了《国故论衡》,“国故”这个词大家就觉得可以成立了。这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胡适第一次对“国学”的概念作了一次分疏。事实上,学术界没有采纳胡适的定义,不约而同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都认可“国学”的另一个定义,即国学是“中国固有的学术”,就是指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唐代的经学与佛学,宋代的理学,明代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以及清代以考据为主要特征的“朴学”。
1938年5月,浙江大学转移到江西泰和,在那里,竺可桢校长请马一浮开办国学讲座。马一浮国学讲座的第一讲,从“楷定国学名义”开始。他提出,时下关于“国学是固有学术”的提法,还是太觉“广泛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他提出:“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是为孔子之教,即后来的“六经”。马一浮认为,国学就应该是“六艺之学”,这是他给出的新的不同于以往的国学定义。“六艺”即“六经”,是中国学问的最初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
马一浮给出的国学是“六艺之学”的定义,其学理内涵最为确切,可以使之与现行的教育体制结合起来,并有助于厘清国学概念的乱用和滥用。这一概念,也使国学回到了中国文化的初典,可以看作是对国学定义最经典的表述,更容易和现代人的精神世界连接,也更容易入于教育体制。当然,作为国学的整体范围,还应加上小学,即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也就是说,经学和小学应该是国学的主要支柱。国学进入教育,主要发用的是“六经”的价值伦理。忠恕、仁爱、诚信、廉耻、和而不同等,就是今天仍然可以发用的价值伦理。这些价值是永恒的。马一浮提出六艺之道、六艺之教、六艺之人三个连续概念,实际上是主张以六艺之道,通过教育途径,使现代人成为具有“六艺”精神伦理的理性之人。
总之,马一浮是迄今最重视“六艺之学”的现代学者,也是将中华文化的最高典范“六艺”楷定为国学的现代学者。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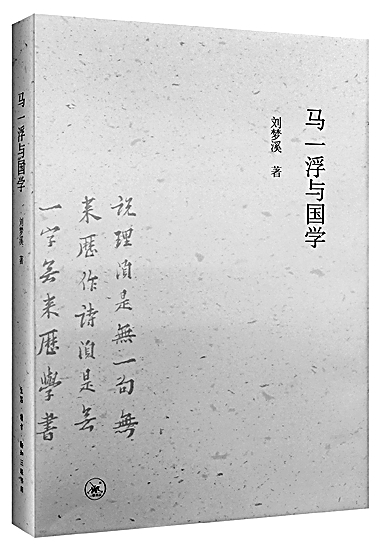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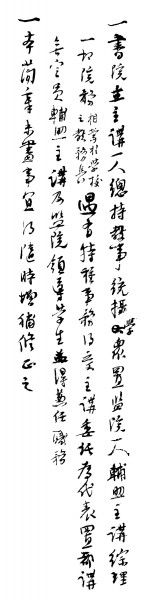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