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让我想起了“擂鼓诗人”田间,想起了以他为代表的敌后“街头诗”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诗人们纷纷投入到反侵略的战争,诗歌成了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形式之一,诗歌创作盛极一时。那时候的诗歌作品,直接作用于那场战争,许多诗作成为了抗战文学的经典作品。同时,我也记起了与田间先生的一些交往经历,记起了那位“抗战老人”的精神风范。
我印象中的田间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常人,是一位有个性的、值得敬重的长者。他是我见到的能称得上“大师”的人中最具有诗人的气质和性格的一位。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调到河北省文联(当时叫省文艺组),那时我刚刚20岁,和田间先生做起了邻居(田间先生家在北京,所以在石家庄也是“单身”)。当时他住在北马路19号省文联的一间15平方米的平房里,办公室兼宿舍。他对诗歌的激情,他的执着,他的敏锐,他的创造力,一直到他的晚年都没有减退。那几年,他几乎隔不了多长时间就出一部诗集,诗集出版后,他裁一些白纸条,用小楷毛笔在上面题上字署上名字,用糨糊粘贴在书的扉页上送给同事和诗人朋友们。当时我为他贴过许多这样的纸条。
在我的记忆中,很少有什么世俗的芜杂的事情能够干扰他的创作。他生活很有规律,很少有社交活动,好像也从没有到外边有过什么应酬。他的生活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每天早晨到食堂买一盆粥,早晨喝一半,留到晚上再把另一半热一热,买点食堂的菜和馒头,就算是一顿饭了;中午饭也是,食堂有什么,他就吃点什么,除了参加会议,我甚至不记得他曾和别人到饭店里吃过一次饭。对于俗常的事情,诸如人际关系之类,他处理起来很不顺畅,所以在我的记忆里,每天他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房子里读书、写诗、写字。
有人问过我:“在写诗上,谁对你的影响最大?”我的回答首先就是田间。不是说在艺术上,我是说在做人上。田间先生身上有一种独有的诗人气质,他刚毅内涵,特立独行,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那样的政治环境下,他也把大量时间用于写诗。当时他担任河北省文联主席、《河北文艺》主编,但他不善于处理琐细的事务。那时候办公室是平房,经常能听到他在党组会上与人发生争执,但他仅有一次对我表示过苦恼。那是有一天吃过晚饭,我问他下午是不是又开会了,他茫然而又有些天真地对我说:“你听到了?一开会就吵。”
田间先生生活中有很多别人不理解的习惯,比如,他每天喝的茶叶都要留下,第二天早上把剩茶叶放在炉子上煮一煮,然后吃掉。有一次我熬了一小锅玉米面粥,给田间先生盛了一碗,他说好喝,一定要我去给他买玉米面自己熬。第二天早晨我还在睡懒觉,田间先生就在门外喊:“小李,快起来。”我本名叫李立丛,所以他称我为小李。我赶紧开门跑到他的屋里,原来他把满满的一大碗玉米面一下子倒进了煮开的沸水里,怎么也搅不开了。后来我还问他:“您在解放区那么久,没有跟老乡们学学怎么熬粥?”田间先生笑了笑,木然地摇了摇头。
田间先生回北京或者去外地时,总是把他房间的钥匙留给我,好替他接收报刊、信函,替他打扫卫生。而且出去时,他爱给我留一些便条(都是用小楷毛笔写的),我记得其中有:“小李,窗台上的饼干时间长了就坏了,你把它吃掉”“刊物不要少了,放好”“小李,去给我买一个能腌100个鸡蛋的小缸,买100个鸡蛋腌上”等等。有一次铁凝提醒我:“郁葱,那些小条你可该留着,都是文物。”我听了以后心痛不已,后悔怎么当时就没有把它们保存下来。诸如此类的故事有很多,现在省文联和省作协流传着许多关于我和田间先生的逸事,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演绎的,无论是真是假,都说明了田间先生独特的性格。那位老人,真是单纯、稚气而善良。
老人平日里话不多,基本上就是没话,但我也见到过他激动的时候。有一次我故意与他谈起“街头诗”运动,老人聊得很兴奋,他对我说,那是他的诗歌最辉煌最有价值的时期,那时候他们把自己写的诗篇写在墙壁上,写在岩石和大树上,看得出来他对那种生活状态依旧充满着向往。我问他闻一多先生是怎么称他为“擂鼓诗人”的,田间先生用浓重的家乡口音说,闻一多的话是这样的:“一声声的鼓点,不只鼓的声律,还有鼓的情绪。”后来我查了查资料,一个字不差。
实际上,我们现在谈“抗战文学”,可能有一个现象或者说现实被忽略了:真正写作于当时的、直接作用于那场战争的、后来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在冀中这一带,田间等诗人创作的诗歌应该说具有最重要的价值。和田间具有同样价值的艺术家,还有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被遮蔽了的摄影家沙飞,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每天晚上,田间先生都写诗到很晚,有时他半夜叫我:“小李,来看看我的诗。”那时我写了诗也经常拿给他看,就像隔代人的交往,很自然,很自如。田间留给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是:我和他做邻居几年,经常请他看我当时写的诗,认为还可以的,他就把那一页折一下,不满意的,他就直接说:“这些不行。”从没有听他说过那些诗为什么“行”,为什么“不行”,他也从来没有对我讲过应该怎样写诗、不应该怎样写诗,这对我后来的影响极大,使我悟出了四个字:诗不可说。
我现在不开作品讨论会,不善应酬,尽量不去讲课,尤其不去“讲诗”,这种“性格”大概就是这样形成的。我总想,也许田间先生想告诉我,诗可“悟”而不可“教”;也许田间先生想告诉我,诗可“异”而不可“同”。所以,他对我说过许多其他的话,唯独没有对我说过原本最应该说的诗歌。我曾经对一位诗友说过,与大师交往,感觉不一样,他们身上那种超出常人的状态,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性情和诗情,同时,也从他们身上获得了某种才情。
其实,当有一天终要离去的时候,仅仅有两点能够留下,也仅仅这两点有意义,那就是人的品格和文字。
还有,一个人厚重的、永恒的背影。
(作者为当代诗人,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郁葱抒情诗》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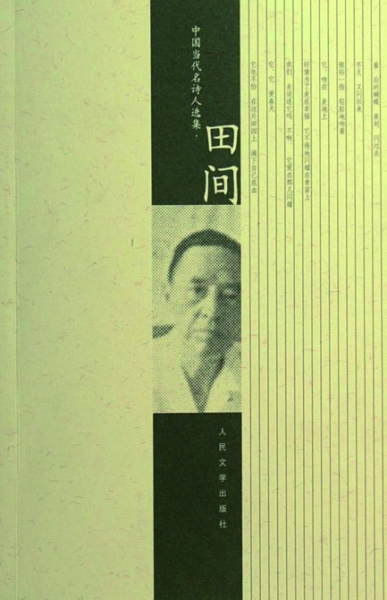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