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我国学界流行“轴心时代”或“轴心期”(Achsenzeit)概念。它是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及目标》(1949)一书中提出的,指西元前8至2世纪这六百年间,印度、中国、古希腊、伊朗和以色列地区不约而同出现了一大批伟大的哲学家或宗教家,由他们提出或在其手中成形的思想观念,奠定了各大文明之后两千多年的走势。按照这一论说,“轴心时代”思维方式一直在深刻影响我们,或者说我们的精神生命一直为其所塑造。这种论说虽提供了学术话语上的一些便利,却不乏局限性和束缚性。
因为它很可能遮蔽或淡化了“轴心时代”之前人类文明的漫长发展。例如埃及文明崛起的时间大约是西元前3500年,两河流域文明大约也在同一时期兴起。不仅有大量文献,而且有大量的出土文物和遗址,来证明这两个文明的存在和演进以及当时文化之高度发达。相比之下,中国文明的诞生较晚。甚至连我们“五帝”即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等传说中的人物,其大概所在时间都明显晚于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
即便只从中国来看,也早在西元前8世纪之前,文明就相当发达了。比如“夏”出现在西元前21世纪。至于西元前16至11世纪黄河中下游一带存在过的“商”,更有大量青铜器传了下来,也有不少相关文献(而非三皇五帝式的传说)流传至今。甚至一代又一代有哪些“王”,叫什么名字,其血缘关系如何,以及做了什么事,都有清清楚楚的记载。“商朝”很发达,其青铜文化之深厚博大,为全世界所钦慕。其技术之高明,直到今天,即便用现代高科技也不能重铸当时铸就的那些精美礼器、食器、饮器、武器等。
西元前11到西元前8世纪之间,又有周代。周是更伟大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周人的思维太现代了。他们很少谈神论鬼,不像其他古代民族(包括希腊人罗马人)那样动辄求神问卜,而更多是依据理性即经验、观察和推理来做出重要决定。尽管不能说周人从此完全摈绝了祭祀,不再占卜,但求神问卜的重要性在周人那里明显降低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周人为了巩固政权,提出了至关重要的天命流转说。他们认为,“天命靡常,唯德是辅”,也就是说,“天命”或天对人们的眷顾是变动不安的,不会永远驻留某一家族、民族或政治集团。如果统治者无“德”或表现不好,对自己属下的“民”不够仁慈,天命就可能转移到另一个集团或部族那里了。这种思想对于后来华夏社会政治理念的演进起到一种强有力的定位或定向作用。可以说直到现在,“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之亲民主张或宣示,最终说来都源自周人的这一重要学说。
对历史上的“西方”做一个考察,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并非现在欧洲和北美等地所能涵盖。通常认为,现代西方文明有两个源头,即古希腊和希伯来文明,都属于“轴心期”文明。但稍稍涉猎一下世界史,便知道它们并非西方最终的源头。西方文明的起源还可往前追溯到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这两个文明都是希腊和希伯来文明的祖先,早在西元前3500年左右就出现了,而古希腊文明大约兴起在西元前8世纪,希伯来文明早一点,大约在西元前12世纪,之间有一个两三千年的时间差。
可是光凭时间先后,能证明一种文明受到了另一种文明的深刻影响吗?为什么不可以说希腊和希伯来文明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呢?
大量证据并不支持这种猜测。事实上,希腊和希伯来文明均非原生文明,而是因恰恰毗邻埃及和两河流域这两个原生文明,利用其技术、理念成果崛起的后发或次生的文明。众所周知,亚欧大陆产生了四大原生文明: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黄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四大文明”有一个共同特点:都诞生于大河流域的大平原或水网密布的大河中下游及三角洲地区,而非诞生在希腊或巴勒斯坦那样的干旱、贫瘠且交通不便的土地上。问题是,为什么四大原生文明都发源于大河流域?
这是因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在与大自然斗争中所掌握的技术极其有限,只有在大自然挑战程度适中的条件下,或者说只有在大河流域,才能大规模发展农业,汲取较多的农业剩余;只有掌握了较多剩余,原生文明——即具有长久生命力并能为后起的文明提供推力的伟大文明——才能萌生并顺利成长。同样重要的是,大河流域通常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不仅适合大规模农耕,而且地势平坦、水道密布,与重峦叠嶂的山区相比,更有利于人员、物质和信息的流通,以及技术发明和思想理念的传播。这显然也更有利于文明本身的诞生和进一步发展。最初希腊人和希伯来人活动之地恰恰不具备这些条件,只有依傍周边已有的技术和文化成果,才谈得上文明的崛起和成长。
稍稍留心一下有关文献、文物和遗址,就会发现古希腊经历了一个“东方化革命”的时代。何为“东方化革命”?它指的是,之前的希腊是一片荒蛮之地,很落后,只是在大量引进东方元素,在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和技术等方面发生“东方化革命”以后,才发展壮大起来。现在大家一提到希腊,脑子里立即浮现种种形象——那些神像何其壮美!那些庙宇何其壮观!围绕神庙的多利式柱形甚至影响了中国人民大会堂的设计。人民大会堂外面怎么会有那些巨大雄伟的希腊式石柱呢?传统建筑语言中根本没有这种概念,那完全是古希腊的东西。可起初,蒙昧的希腊人根本不知道神庙为何物。神庙建筑的样式和风格、祭拜仪式的细节、人员的配备和管理,甚至神庙概念本身,统统都是从埃及和西亚“拿来”的。不仅如此,希腊人曾大规模留学埃及,雅典改革家梭伦、斯巴达改革家吕库古、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等许多希腊名人,都曾去埃及,师从那里的学问家即祭司。
像希腊文明一样,发祥于现以色列、约旦、叙利亚等干旱少雨之地的希伯来文明也是一种次生文明。在其早期历史上,亚伯拉罕所代表的希伯来人先祖曾游历于两河流域的乌尔城一带,后来迁居“迦南”,一个相对于文明中心更偏远的地方。但正是在两河流域,以色列人学到了很多东西,《圣经》中的创世故事、大洪水故事、诺亚方舟故事便是最明显的例子。再后来,游牧的希伯来人又客居埃及几百年。正是在此期间,他们学会了农业和定居。
完全可以说,没有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便没有希腊和希伯来文明。同样地,中国文明在“轴心时代”之前,已有夏商周的丰厚积累,不能因为时兴一个学术概念,便有意无意夸大其重要性。那几百年里产生了孔子、老子、佛陀、以色列先知和希腊哲学家,的确非常重要,但之前的文明历程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同样居功至伟。“轴心时代”概念的确给学术界提供了丰富的话题,但我们不能受其束缚。我们不能偷懒,跟在西方学者后面亦步亦趋,过分夸大“轴心时代”的重要性,仿佛之前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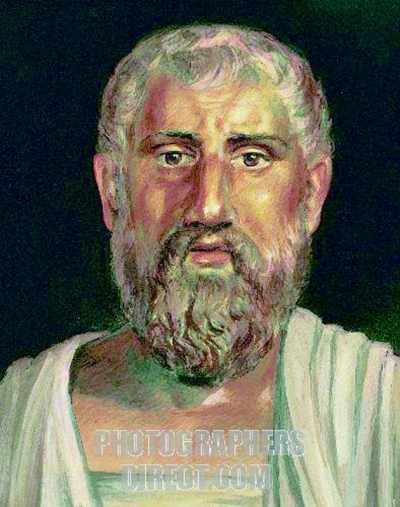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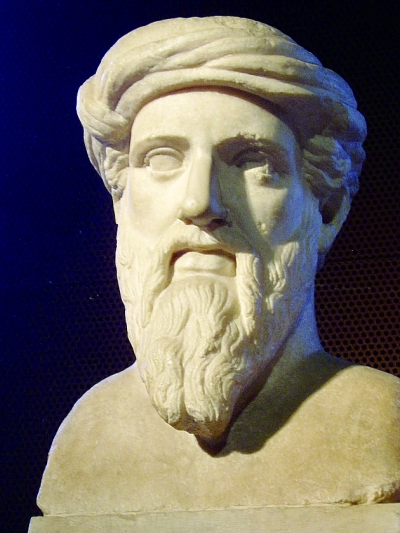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