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月的日历即将翻过,便意味着“三八妇女节”就要到来,当然,还意味着年年讨论的女性问题也将再次被提起。与往年不同,微信上关于女性问题的讨论从春节那天便席卷而来并持续至今。先是春晚小品是否有女性歧视的讨论,引发了无数观众和手机用户的热议;紧接着的另一个热议出现在大洋彼岸的奥斯卡颁奖礼上。在《少年时代》中饰演母亲一角的帕特丽夏获得了最佳女配角,在依惯例念完感谢名单后,她提出了好莱坞男女同工同酬问题:“感谢每一位纳税人和每一位公民的母亲,我们曾经为了别人的平等权益而战斗,现在让我们为男女同工同酬战斗,为美国所有女性的平等权益战斗。”这番话诚恳、切中,得到了整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事后美国媒体也都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发表了她的获奖感言。这是卓有意味的一刻。
也许话题终究会变旧,但它带来的思考却不应随风而去——尽管全球化的妇女解放运动已历数百年,但那并不是“完成时”,而是“进行时”。今年开春女性话题在坊间的持续热议使人们再次认识到,无论是否是在“三八节”这天,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重申男女平等、女性立场、女性权利依然是如此必要。
点亮幽暗之地
如果把中国文学史比作一条无穷无尽的大路,那么作家则是道路上的路标:从这段开始,我们进入了那个叫司马迁的领地;过一阵,我们将到达李白之地,很快,我们就在不远处看到了杜甫,还有苏东坡、关汉卿、曹雪芹、蒲松龄……讨论这些大作家及其作品时,我们几乎不用辅助手段。因为他们在光亮处,他们已经被命名,被确证,被视为经典。但是,一路走来,你会发现大路上的女作家少之又少。只有李清照,或者,还有蔡文姬?无论怎样,在千年文学的大路上,被女性写作者命名的路标好少,少得可怜。
岂止是女作家,关于女性人物及其生活,我们的正史记载都少之又少。女性生活在沉默之地,这是事实。因为几千年来绝大多数女性的受教育权是被剥夺的,她们受困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习俗,这是中国历史上女作家数量稀少的原因。当然,1919年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五四时期开始出现了女作家群体,我们也逐渐在文学作品中看到她们笔下的女性生活——那种不仅仅生活在才子佳人故事中的女性生活,那种有人间烟火气的女性生活。但是,还是不清晰。关于她们的一切影影绰绰。因而,要讨论百年女性写作,我们得点燃一支火把,要理解创世纪者的工作,还需要蹲下身子,把火把贴到历史现场。
首先,那封发黄的信将被我们发现。“中国女作家也太少了,所以中国女子思想及生活从来没有叫世界知道的,对于人类贡献来说,未免太不负责任了。先生意下如何,亦愿意援手女同胞这类事业吗?”这封信写于九十多年前,1923年9月1日。写信的女子叫凌叔华,收信人则是她的老师周作人。
是的,当时中国女作家实在是太少了。回到那个历史空间,我们所能想到的受全社会瞩目的女性作家只有冰心(虽然当时陈衡哲也开始写作,但她的读者相较于冰心少之又少)。冰心受到的社会关注是空前的,她写她作为女学生的生活,以及她面对世界的感受。清新、纯洁、亲切、温暖,女性生活的一小块帷幕由此被拉开。作为冰心的燕大学妹,年轻的凌叔华因为看到女性生活“从来没有叫世界知道”,也便意识到了中国女性写作的革命性意义。她有意为我们提供一群“时代”之外的闺秀生活,讲述她们内心世界的欲望与隐秘。以被众人忽视的对象为对象,凌叔华书写了“高门钜族的精魂”(鲁迅语)。
但更惊世骇俗的是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小说中的莎菲是迷人的和令人惊艳的,她不是娜拉、不是祥林嫂、更不是子君,在爱情面前,她从来不是被动的“小白兔”。《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横空出世表明,女作家和她的女性人物由幽暗之地来到了光亮之所在,丁玲使我们重新认识女性作家和女性人物的勇敢。
问题是,为什么在1919年之后,中国开始有一批女作家集体出现而在这之前没有?注意到陈衡哲、冰心、凌叔华、冯沅君、庐隐、苏雪林、石评梅等人的教育背景是必要的,她们都是女学堂的毕业生。女学生的出现对于中国女性写作具有重要意义。女学生们最早出现在外国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女校中,之后,中国人自办的女校陆续出现。随着1907年清政府《学部奏定女子小学章程》26条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39条的颁布,女学堂在中国合法化,女学生群体日益壮大。
女学生是中国第一群以合法的名义离开家庭进入学堂读书的女性。这使几千年只能在家内生活的良家妇女进入了公共领域。不缠足、走出家庭、进女校读书、与同龄女性交流、出外旅行、参与社会活动、与男性交往……都是现代女性写作发生的客观条件。如果说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只是为女性写作提供了客观条件的话,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则提供了一批具有现代主体意识的女性,她们是勇于用“我”说话、勇于发表对社会的看法、勇于表达爱情、勇于审视内心、也勇于向传统发出挑战的新青年。
今天看来,五四时期关于女性价值的讨论多么有意义。鲁迅、胡适、周作人、李大钊、叶圣陶、罗家伦等人都参与了妇女解放的讨论,发表了重要文章。在《美国的妇人》中,胡适提出了他著名的“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做一个良妻贤母何尝不好。但我是堂堂地一个人,有许多该尽的责任,有许多可做的事业,何必定须做人家的良妻贤母,才算尽我的天职,算做我的事业呢?”彼时讨论的共识是,一个女性是属于社会的、独立的个人,即使她不是妻子、不是母亲,依然应该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她的生命存在依然是有意义的。想来,我们时代每一位女性的生活都受益于这样的讨论,正是具有鲜明女性立场的社会讨论才最终改变了中国女性命运。人的意识和女性意识的苏醒使中国女性成为现代女性,也使她们中的一部分人拿起笔,以书写照亮自己,也以书写照亮姐妹们喑哑的生活。
“让那些看不见的看见,让那些听不见的听见”
与五四初期的冰心、庐隐、凌叔华等人相比,丁玲、萧红、张爱玲的写作更加成熟和深入——前者的意义在于拉开了书写不为人知的女性生活的序幕,而后者,则早已不停留于此,她们不仅仅书写女性生活,更提供与男性不同的立场和看待世界的方法,视角独特而深刻。当然,相比而言,后来的写作者们的生存环境早已大不相同,此时的她们更为自由,已不再只是女友、妻子、母亲,她们逐渐成为一个挣工资者、独立撰稿人、在战火中奔波的逃难者、到圣地延安的革命青年、自由行走世界的旅人以及表达不同意见的社会公民。
出版于1941年的《呼兰河传》是萧红的代表作。你很难知道萧红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或变了什么样的魔术,当她在《呼兰河传》中“话说当年”,读者便会自然而然地回到“过去”,会自然而然地变“小”,有如孩子——像孩子一样感受世界不染尘埃的美好,也会体察到陈规习俗对于一个人的扼杀,对异类的折磨。那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一幕,因为长得不像12岁的高度,那位小团圆媳妇被她的女性亲戚们“好心地”抬进了大缸里,大缸里满是热水,滚热滚热的热水。“她在大缸里边,叫着、跳着,好像她要逃命似的狂喊。她的旁边站着三四个人从缸里搅起热水来往她的头上浇。”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只是因不似“常人”而“被搭救”也被毁灭了。我们只能和小说中那位女童一样大睁着眼睛看小团圆媳妇的挣扎和死亡。萧红目光开阔,她写的是作为受害者的女性、作为迫害者的女性以及提供这种愚昧土壤的民族性。
也是在1941年,丁玲发表了她的两部重要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被日本人玷污,同时也为抗日队伍送情报。那么,她是贞洁的吗?我们如何理解这位女性的处境?还有《在医院中》的陆萍,这位初到延安的知识青年发现了个人与环境的矛盾和冲突时,她所做的质疑是有意义的吗?她有没有必要把她的困惑和不满写下来,发表出去?文本里的立场和态度矛盾交错,偏僻而不同寻常。为什么学者们如此关注这两部作品及作品中所蕴含的丰富性?因为这是站在女性立场、边缘立场的作品,更是一位书写者对于生活和时代的深入而切肤的思考。两年后的1943年,张爱玲的《金锁记》则显示了另一种能量,它甫一发表便被傅雷视为张爱玲的重要代表作。曹七巧为金钱的锁链所困,被迫嫁给了软骨病病人,多年后,儿女长大成人,她则变成为儿女戴上黄金锁链的人,她限制他们的自由,也戕害他们的人生。《金锁记》为我们勾描了金钱制度下的典型的女狂人形象,直到今天,这位女性依然栩栩如生。
20世纪40年代的女性写作,尖锐、锋利、别具洞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为不可忽视的路标。如果说40年代中国女性写作代表了一种高度,那么新时期至今以来的女性写作则是另一个黄金期。你很难忘记王安忆的《我爱比尔》。女主人公阿三一次次渴望融入这个时代的文化氛围,成为时代文化的一部分。你也很难忘记铁凝的《永远有多远》,女主人公白大省热情、简单、仁义而宽厚,渴望成为深得时代文化精神的“西单小六”,但总是不能如愿。作为艺术人物,阿三的幸运在于她最终没有被时代以及西方文化接纳,而白大省的魅力则在于她与整个时代风潮的格格不入和对仁义美德的守候——缓慢的反应、笨拙的转身以及空怀一腔热情,使她成为这个时代的“特立独行”之人。阿三和白大省是文学史上两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怪里怪气”的女性形象,经由这两个人物,作家王安忆和铁凝表达了她们的冷静思考,即,在时代潮流面前一个女人、一个人如何保持主体性与独立性。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想起当代文学史中那些出自女性作家之手的作品。宗璞的《红豆》、茹志鹃的《百合花》、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谌容的《人到中年》、铁凝《玫瑰门》、王安忆《长恨歌》、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归去来辞》等。当我们把百年来的女性作品连缀在一起,会发现这些女性作家固然书写的是女性生活,但同时也是对那种被时代潮流遗失的生活的记取,是对女性精神和女性立场的重申。那些沉默的、那些无故牺牲的、那些处于幽暗之地的种种能最终进入我们的公共生活、历史空间,是因为她们的倾听与书写,她们“让那些看不见的看见,让那些听不见的听见”。
刻录下另一种女性之音
“句子,句子!没有什么比句子对一个作家更重要的了”,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说。句子并不只是句子那么简单,它还是声音和调性的寻找。“这就是一位妇女必须为她自己所做的工作:把当代流行的句式加以变化和改编,直到她写了一种能够以自然的形式容纳她的思想而不至于压碎或歪曲它的句子。”在文学史上,独特的属于女性表达的声音和调性将在优秀作家那里得以完成。比如在简·奥斯汀那里、艾米莉·勃朗特那里、在伍尔夫那里,以及在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那里。在中国现代早期女作家冰心、庐隐、凌叔华那里,那种来自女性的句式表达是生涩的和别扭的,完美表达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实践,也需要作家具有开拓的勇气。寻找是持续的,到40年代,在萧红、张爱玲那里,一种更为自由和成熟的独属于女性的声音与句法正逐步形成。
我想,当代文学史上令人最为心碎的声音和句式应该属于那位矿工妻子蒋百嫂。她是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的人物。蒋百在矿难中失踪,蒋百嫂因此便害怕黑夜。有一天镇上停电了。“蒋百嫂跺着脚哭叫着,我要电!我要电!这世道还有没有公平啊,让我一个女人呆在黑暗中!我要电,我要电啊!这世上的夜晚怎么这么黑啊!!”如果不是迟子建,那位卑微的处于黑暗中的女性的内心哀痛将怎样诉说,将向何人诉说?
那些不可见的人们、那偏僻世界里的叹息、最底层人民不能言说的苦痛都被迟子建看到、听到和感受到了。在当代作家林白、方方、李娟、塞壬、郑小琼等人的作品里,你也会听到自1919年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那种低微、富饶而强有力的女性声音。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和中国女性境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代文学领域,难以数计的女作家们以丰硕的创作实绩丰富了中国当代女性写作,也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本身。
2015年初走红的女诗人余秀华更令人惊讶。很难忘记余秀华在电视节目“锵锵三人行”中读诗的声音,含混、呜咽、痛楚,那是我们时代受伤者的声音,与那种字正腔圆的表达完全迥异。无论你读过多少诗,听过多少诗朗诵,你依然会被这种声音打动。你会强烈意识到,那是有着鲜活人气的声音,不是玩弄诗艺的精英腔调。作为疾病的承受者,她写下了我们感受到的但无法成诗的那部分,她站在我们“不可见处”,写下的是被我们习焉不察的时代之音。这样的声音再次使人意识到,女性写作有独特的个人立场和世界观当然是宝贵的,但更重要的是寻找到属于女性的声音和句法,哪怕是农妇的、疾病的声音。
我以为,女性写作者,或者,更宽泛地说,女性艺术工作者们的女性立场在我们的时代弥足宝贵。看今年春晚时,我无比怀念故去多年的赵丽蓉女士。还记得小品《如此包装》和《打工奇遇》吗?那么多的浮夸、浮华,一摞一摞的金钱,都不能阻挡老太太最为朴素的听从个人内心的表达。也许我们最应该记得的是《英雄母亲的一天》,无论小品中的编导怎样乔张做致,这位母亲都有她接地气的理解力和价值观。小品中的老太太是普通农村女性,也是没有多少文化的人,但是她有看法、有立场、有勇气。在赵丽蓉主演的小品中,借助她有别于普通话的带有浓烈唐山味道的地方口音,借助她独特的属于民间女性的句法,你可以看到彼时流行文化和流行价值取向的浮夸和苍白——赵丽蓉的小品之所以一问世便家喻户晓流传至今,在于小品深植于内的幽默、尖锐、讽刺,以及那种身处低微面对“高处”却不卑不亢独具我见的艺术态度。
作为演员,赵丽蓉的诠释是洗尽铅华、深具民间立场和女性精神的。2015年的春晚中,社会上流行的对女性生活的看法也都被编排进各种小品中,引发了阵阵笑声。但是,这些小品中关于女性的台词大都来自于他人的看法和她们对他人看法的演绎,观众看不到女性如何看世界,观众无法听到女性真正的内心声音——随着赵丽蓉的离世,春晚的女性精神和女性声音出现了严重匮乏,今年春晚,无论小品编导是否是女性,无论演员是否是女性,都再没有了女性立场。我们看不到下一个赵丽蓉,也听不到“中国帕特丽夏”的声音,这是多么令人遗憾和惋惜的事情。
作为双刃剑的性别立场
重新执起女性精神的火把,站在女性立场言说于今而言尤为迫切——今天的电视荧屏里,我们能听到那些工厂女工们的声音吗?我们能听到基层农妇们的声音吗?我们能听到那些单身母亲的声音吗?她们的声音是微弱的。与之相对,我们却常在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上听到对女性的肆无忌惮的嘲笑——对年老女人羞辱、对大龄未婚女讽刺、对容貌丑陋女性歧视。当一个女性不是妻子也不是母亲,她的生命和生活是有价值的吗,她应该受到尊重吗?如果是,为什么全社会都在焦急催促她们结婚生子?在我们这个认为“女性也是半边天”的国度里,那百年前早已明确的答案已然变得暧昧诡异,当下的语境里,似乎只有寻找到另一半或者成为母亲的女性才可以受到尊重,这实在是我们这个文明和开放社会该警惕的。
当然,于写作艺术而言,永远激进地手持“性别”火把对女性写作本身可能也是危险的。这需要辨析。女性的愤怒和控诉有可能遮蔽作家对作品艺术品质的追求。伍尔夫将西方文学史中的女作家分为一流与二流:“在一些二流的女作家那里更是可以时时见到这种情况,表现在她们所选择的题材,以及她们的不自然的逞强好胜或不自然的温良驯顺。更甚的是虚伪态度的广泛渗透……其艺术想象或是太男性化,或是太女性化,从而失去了自身的完美整体性,也即失去了艺术的最根本的品质。”她强调艺术家的艺术品质而非性别,尽管性别是重要的,但“任何人若是写作想到自己的性别就无救了。”对此,我深以为然。
一位真正优秀的女作家,即使不借用性别的火把,依然能够在文学史上刻下属于自己的路标。因为她要关注的是所有边缘的和弱势的生存,女人的,男人的,以及全人类的,她的艺术专注力最终转向的是非个人的,她的小说最终要有更多的社会责任和更少的对个人化生活的沉溺。当然,事实上,在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史上,上文中提到的诸多作家,丁玲、萧红、张爱玲、王安忆、铁凝、迟子建等,也早已摆脱那支性别的火把——当我们浏览1919年以后的作家路标时,会很容易看到她们的身影,因为,她们已经成为火把本身。
(作者为学者,批评家,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出版学术专著:《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姐妹镜像:21世纪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魅力所在:当代文学片论》。配图均为资料图片。)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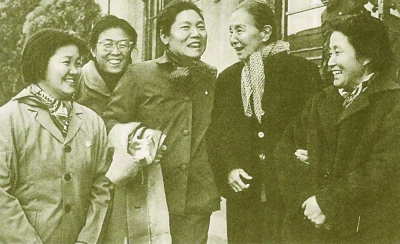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