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材施教”是一条古老的教学原则。于永川先生在概述“中国古代教学原则”时,将“因材施教”作为第一条教学原则。他概括道:
“显而易见,‘材’是指学生的道德修养、意志性格、知识水平、接受能力、才能爱好等方面的差异;‘教’是指德智体诸方面的教育。因材施教,就是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因人而异,区别对待,量体裁衣,对症下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总之,要知人善教”。
2005年,钱学森先生提出了他的问题:“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那么问题来了,一直以来被奉为圭臬的因材施教能否培养出杰出人才、或者说具有极强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我们尝试从几名创造性人才的成长个案中寻找线索——这类人才非常类似“黑天鹅”。也许他们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反思“凡天鹅皆是白色”的判断,同时给我们以启发。
成长目标的不断变换与教育支持
卡尔·R·罗杰斯(Carl Ransom Rogers,1902-1987)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人本心理学的创始人。在其“自述”一文中,他讲述了自己走上心理学道路的曲折历程:
童年时,他对夜间活动的大飞蛾着了迷。后来又在家庭农场饲养小鸡、小猪、小羊和小牛,生发出对农业科学的兴趣。
在威斯康星开始大学本科生活,主修农学专业。
受“情绪激昂的学生宗教会议的影响”,其职业目标从农业科学家变为牧师。之后转专业,由农学转到历史学专业。
1922年,到中国参加一个国际性的世界学生基督教同盟会议,期间产生深入的思考,“认识到真挚而诚实的人们会信仰截然不同的宗教教义”,对他产生重要影响。
研究生入读纽约联合神学院。在神学院和同学向院方提出,“希望允许我们成立一个没有指导老师的研讨会,课程设置也由我们自己的问题组成。毫不奇怪,院方被我们弄糊涂了,但他们还是批准了我们的请求”。这一由学生组织的课程导致了意外的结果(仔细想想,确实太意外了!)——“大多数研讨会成员在思考自己提出的问题时,认为自己最好离开宗教工作”。罗杰斯也是其中一位。
开始在联邦神学院一墙之隔的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选修课程,于1928年和1931年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走向心理学领域。
可以说,在罗杰斯走向心理学的过程中,我们少有看到因材施教的作用,在其每一阶段的成长中,他的才具和方向在不断变化和发展。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成长与罗杰斯有些相似。少年维特根斯坦爱好机械与技术,十岁时就制出过一台缝纫机,其最初的志向在于物理学。随后维特根斯坦又立志成为一名工程师,并于1908年进入英国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攻读航空工程空气动力学学位。在这期间他接触到罗素与怀特海合写的《数学原理》,之后才辗转走向哲学道路。
认识自己对于罗杰斯和维特根斯坦而言,似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中,教师的因材施教很难说对其最终成为创造性人才发挥出作用,反而是他们所经历的教育制度、教育系统以及教师的教育理念对其人生发展产生的一系列重要影响和支持,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例如,威斯康星大学允许他们自由地转专业;例如,联合神学院允许学生自行开设没有教师的课程,这一课程导致大部分学生疏离了宗教,这个结果应当不符合神学院的培养目标,但却对许多学生的人生发展是决定性的,在本质上符合教育规律;哥伦比亚大学允许罗杰斯选修课程,并进入教师学院学习。以上这些都不是教师的因材施教,而更多是制度对一个杰出人才在自我寻找、自我认知中提供的帮助和支持,这样的教育支持在我们思考“钱学森之问”时无疑是必须予以重视和反复思考的。
无用与有用
乔布斯是当今时代最典型的一名技术领域的集成创新者。他并非美国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因为其进入美国里德学院一个学期就退学了。退学这一行动取消了所有大学阶段教师对乔布斯因材施教的可能,仅保留了自主学习这一核心因素。2005年乔布斯受邀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发表演讲,他讲到自己在上大学6个月之后,不知道这样念下去究竟有什么用,于是决定退学。虽然当时有些害怕,但他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
退学后他不用去上那些他毫无兴趣的必修课了,于是跟随好奇心和直觉开始旁听那些看来比较有意思的科目,其中一门就是里德大学提供的全美国最好的书法课,当时,他压根儿没想到这些书法知识会在他的生命中有什么实际运用价值。但是10年之后,当他们设计第一款Macintosh电脑的时候,这些东西全派上了用场。他把它们全部设计进了Mac,这是第一台可以排出好看版式的电脑。
乔布斯在退学后精神极为自由。因为他退学,老师因材施教不再可能,来自老师、学校规制化知识体系的束缚被放弃。这种最大的自由也是最大的迷茫,但也孕育着最大可能。在这样的自由状态、或者说空去目标的状态中,书法课仅因为兴趣进入他的视野。这不是因为来自教师的培养目标与因材施教,也不是因为来自个人的成长目标而进入他的视野。这门课程与后期Macintosh电脑的排版系统功能创新奇妙地联系在一起,也间接与iphone和ipad所追求的极致工业美感联系在一起,在乔布斯身上从“无用”成就了“大用”。
当然,我们仍然需要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处于没有培养目标和没有成长目标的人有很多,为何乔布斯成了创新人才,其他大部分人不但没有成才,有些甚至迷失了呢?这时我们需要注意到乔布斯身上的因素。第一,他在这种情况下保留了坚定的自信心,“我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他曾说过“要坚信,你现在所经历的将在你未来的生命中串联起来”。其次,他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坚持着极其艰难的自我探索和学习,包括参禅以及在里德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旁听,他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求知欲,这是非常少见的情况。第三,我们注意到在这样的过程中里德学院的宽容,允许他退学后自由旁听,注意到他(养)父母对其自我选择的支持和宽容,这些东西似乎构成了一种外在的鼓励自我选择和自我负责的环境,而我们在回答“钱学森之问”时,必须珍视上述个人品质和环境对创新人才产生的作用,如何维护这样的品质,提供这样的环境,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付诸行动。
种豆得瓜与宽容的农夫
冯唐是当代中国一名作家,还是诗人、医生、商人、古器物爱好者。他是北京大学和协和医科大学的校友。1990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先军训一年,之后进入生物学系学习医学预科课程,然后进入协和医科大学的8年制医学教育。那时直接考入协和8年制的学生是高考中的佼佼者,他们以成为良医为人生愿景。北大的教师知道协和的培养目标以及对学生的期望,在教学过程中因材施教了;协和的教师当然也因材施教了。但是,冯唐在获得一个临床医学博士学位后又去攻读了MBA,在从事咨询业和实际的商务工作之余,坚持写作,成了一名作家!
医学教育职业感很强,其培养目标十分清楚,就是培养出良医,其生均教育成本很高。以这样的目标衡量对于冯唐的医学教育,我们大致可以发现其课程教师以医生为目标的因材施教是失败的,以医生为目标的教育投资是无效的,但是失败的医学教育却培养出一名好作家,这非常类似种豆得瓜。
种豆得瓜对于医学教育和作家而言,冯唐不是第一位,也不会是最后一位。历史上另外还有三位,英国著名作家毛姆,还有我国著名作家郭沫若、鲁迅,都是弃医从文。再看看其他行业,杭州师范学院英语系的毕业生马云,成为电子商务领域的创新者;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矿产一系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的毕业生温家宝,成为共和国的总理。
以往,我们总是视这些人为个案和例外,少有研究其中的教育因果。其实,我们如果把视角调校一下,会发现这样的“个案”有很多,而研究他们身上的教育因果很有意义。如果冯唐所经历的每个教师都极其严酷地抱定因材施教的原则并且在实践中不折不扣的践行,冯唐会有机会成为作家吗?因材施教中存在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因材施教的局限性在于教师对学生之“材”判断存在主观性,教师经验存在局限性,教师想象力存在着“天花板”,教师的“教”存在限度,而学生却是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主动性,他们不是石材、更不是木材,而是生机勃勃的人,学生之“材”在学习和教育过程中必然发生变化。对于这种情况,从农夫的角度打一个比喻,当其在大豆田中发现一株异类植物而将其连根拔除,种豆得瓜便毫无可能,但农夫若对这株奇怪植物保持宽容,愿意等等看,有着好奇心研究一下这是何种植物,甚至冒险承担大豆减产的风险,种豆得瓜才有可能。冯唐的医学教育中几乎没有什么课程为写作而设置,也没有什么课程意图培养学生的商业潜能。但冯唐的教育中一定有一些东西,激发起他自我探索和持续的学习动力;有着某种宽容,允许其生发出对写作和商业的兴趣和追求。
总之,我们应该看到创造性的学生似乎不是“因材施教”的结果,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少有老师可以预见他们的创造性流向。他们的创造性方向不是按照教师安排的轨道亦步亦趋可预见地发展出来的。了解这一点对于教师十分重要。正是学生A自己基于旺盛的好奇心、生命力以及自我持续一生的学习和追求,为A这一名字赋予了最终的意义。因此,从这个视角看,回答“钱学森之问”,我们需要超越因材施教。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兼元培学院副院长,三级研究员)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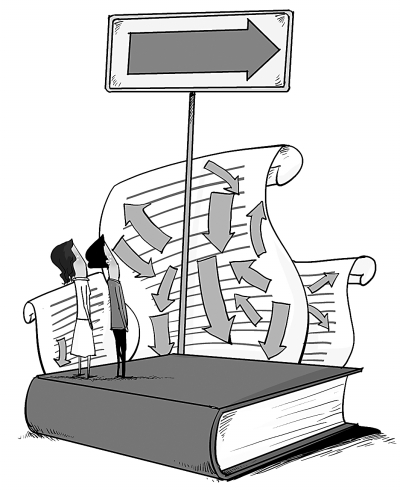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