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编译局,有这样一位老人:他18岁来到这里,如今已默默耕耘63个春秋。几十年间,他目睹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风云变幻,见证了新中国编译事业的起步与发展,参与了中央编译局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贡献了全部智慧和力量。他是顾锦屏,一位不忘初心、笃信马列,以编译事业安身立命的马克思主义者。
“‘先天’不足‘后天’补,誓由外行变内行”
20世纪50—60年代,《简明哲学辞典》曾作为一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难以替代的工具书,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广受欢迎。这部由苏联哲学家尤金和罗森塔尔主编的辞书,1955年由中央编译局翻译室哲学组译成中文。初入编译局的顾锦屏全程参与了这项工作。
时间回到1949年。这一年末,华东革命大学附设上海俄语专修学校成立,正在江苏太仓师范读书的顾锦屏一考即中,成为上海俄专第一届学生。此时,顾锦屏16岁。
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为了向苏联学习建设经验,各行各业急需俄语人才。顾锦屏分秒必争,开始学习俄语。1951年9月,中央组织部决定从上海俄专调25名学生赴北京工作。学校公布的名单中,顾锦屏赫然在列。18岁的他来到中共中央俄文编译局(1953年与中宣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为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从此再未离开。
参与翻译《简明哲学辞典》,是顾锦屏到编译局后的第一项任务。此时,《简明哲学辞典》在苏联已修订了4版,从语言到内容都十分艰深。捧着沉甸甸的俄文版清样,顾锦屏心里也沉甸甸的。“在哲学面前,我完全是一张白纸。俄语只学了一年半,功底并不扎实,能做得了这份工作吗?”
“我看过你的档案。你是读的师范,我也读的师范。只要你好好干,认真学,肯定能够胜任。”编译局首任局长师哲的一席话,坚定了顾锦屏的信心。
白天,顾锦屏全身心投入辞典翻译工作,认真向何匡、刘水、林利等前辈请教,将他们改得满篇红的稿子当作“活教材”;晚上则一头扎进书斋,带着白天的总结和思考研读毛泽东著作、苏联理论书籍,汲取哲学养分。他买来中、俄文版《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对照着读,既学俄语,也学理论,还时常翻译一些苏联理论文章,请前辈审定后发表在《学习译丛》上。“‘先天’不足‘后天’补,一定要从外行变内行!”顾锦屏暗下决心。
历经3年集体攻关,新中国第一部哲学辞典翻译完成。紧接着,顾锦屏又参加了列宁《哲学笔记》的翻译和译文校订工作。到1956年《哲学笔记》出版时,顾锦屏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哲学知识和翻译经验,但也戴上了一副几百度的眼镜。
“哲学方面的翻译问题,问问顾锦屏,基本上就解决了”
“小孩儿”,是顾锦屏刚到编译局时一些老同志对他的称呼。及至1956年编译局翻译《列宁全集》时,“小孩儿”已经担起了大任,负责第14卷即《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审稿和定稿。
在重任面前,顾锦屏猛然发现,原来的知识储备不够用了。“马列著作博大精深、包罗万象,仅仅掌握一些哲学基本概念远不能精准理解。”为了深入理解《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顾锦屏不仅认真向苏联专家请教,还系统梳理了列宁的批判对象——马赫主义的哲学思想,并恶补了欧洲哲学史方面的知识。
经过全局同志的日夜奋战,1959年,《列宁全集》第一版共38卷全部译完,向新中国10周岁生日献上一份大礼。顾锦屏和同事们还没来得及休息,就投入了新的战斗——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顾锦屏参与审稿定稿的《马恩全集》第一版第3卷即《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部内容精深、涉及问题极广的论战性巨著,在其《圣麦克斯》部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进行批驳而引用的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中的文句十分晦涩,翻译起来难度极大。“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的教导给了顾锦屏和同事们攻坚克难的决心。
在堆满书籍和参考资料的办公室里,大家经常聚在一起,推敲原著、研讨难题,聆听苏联专家讲解原著要义。
经过两年努力,这部鸿篇巨著终于面世,受到高度肯定。不久,顾锦屏被任命为中央编译局马恩室副主任,成为名副其实的业务骨干。
此后数年间,顾锦屏承担《马恩全集》第一版第20卷中《反杜林论》的审稿、定稿工作,参与了《共产党宣言》《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多部作品的校审工作。日积月累,他已经能熟练地运用俄语和德语译校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走进原著,马克思的形象更加清晰,也更加亲近了。”顾锦屏自认,这是他一生中成长最快的岁月,而那时在编译局一些同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哲学方面的翻译问题,问问顾锦屏,基本上就解决了!”
“‘咬定青山不放松’,对我而言,这座‘青山’就是马克思主义”
十年浩劫结束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马列著作编译事业也开创了新局面。1978年,顾锦屏出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站在新的起点上,他深感责任之重。
为了打造一支高素质翻译队伍,他四处奔波、广邀贤才,积极为年轻人铺路搭桥,争取业务培训、出国深造的机会;为了提升经典著作编译水平,他多次出访,与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等国际马列著作研究机构建立联系。他为编译研究人员的应有待遇据理力争,也为优秀人才的流失痛心疾首。
“白天忙局务,晚上忙业务”是顾锦屏对那段时光的总结。只要不出差,他总会在晚饭后返回办公室。一盏孤灯,一杯清茶,伴他执着于自己钟爱的编译工作。
1982年,经中央批准,《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60卷本)编译工作正式启动。到1990年底,第二版全部出齐。编译局没有照搬《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五版,而是进行了大量资料收集和编辑工作,这也成为我国自行编辑的收文最全、资料最翔实的列宁著作集。顾锦屏利用挤出来的时间,参与了其中3卷的校审工作。
1986年,按照中央决定,《马恩全集》中文第二版(70卷本)编译工作启动,顾锦屏参与了部分卷次的修改和审定,不久前,由他校审的第26卷刚刚出版。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一时间,马克思主义“失败论”“过时论”大为流行。为此,顾锦屏撰写了《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几点思考》等文章,以坚定的信仰、求实的态度和令人信服的说理,在一片喧嚣和迷茫中表达了追求真理、捍卫真理的精神。
“‘咬定青山不放松’,对我而言,这座‘青山’就是马克思主义。我1953年入党,60多年来,听到过各种论调,经历过无数次风吹浪打,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未动摇。搞马列著作翻译,关系到党的指导思想,关系到理论是非,来不得半点马虎!”顾锦屏身体力行。
“我们这些老人对马列主义怀有深厚感情……总想尽些绵薄之力”
这段时间,顾锦屏正忙于《马恩全集》中文第二版(70卷本)编译以及《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各卷“前言”的审读修订工作,目前,前19卷“前言”已审读完毕。
“前言”意在介绍各卷的写作背景和主旨,重要性不容小觑。“原来的‘前言’写得比较好,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列宁在各个时期的革命实践活动和理论贡献,但也存在一些不妥之处。”顾锦屏翻开摆在案头的第18卷,认真而严肃。“‘前言’中有‘考茨基和阿德勒主张用马赫主义的认识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表述,这显然是将考茨基作为列宁的批判对象了。但据我考查,第18卷中列宁共3次提到考茨基,一处将他作为俄国马赫主义者的攻击对象,一处引用考茨基的话批判康德的认识论,一处则将考茨基与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梅林等并列为社会主义的权威人士。可见,此时的考茨基尚未成为修正主义者,还不是列宁的批判对象。中文版‘前言’显然受了俄文第5版编者所撰‘前言’的影响。我在审读中把考茨基的名字删去了。”
顾锦屏始终不忘恩格斯的教诲:“翻译马克思的著作是真正老老实实的科学工作。”他总是字斟句酌、精益求精,不辞辛苦地在马列经典著作的文字中探寻摸索。他早已于1996年退离了领导岗位,2004年办理了退休手续,却始终奋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和研究的第一线。“退而不休,在编译局是常态。我们这些老人对马列主义怀有深厚感情,只要身体还好,总想尽些绵薄之力!”
2004年,中央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顾锦屏作为经典作家重点著作译文审核和修订课题组负责人之一,为编辑方针、校订原则和编写要求的制定倾注心血,还承担了译文的审核修订工作。2009年,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五卷本《列宁专题文集》正式出版,被中央领导同志赞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标志性成果”。2012年,顾锦屏担任副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列宁选集》第三版(修订版)、《马克思画传》《恩格斯画传》和《列宁画传》相继出版。
“翻译工作特别是对译本的修订工作,是一个对原著的认识不断加深的过程,是一个从相对真理接近绝对真理的过程。随着我们认识的逐渐加深,可能会发现原来没有发现的错误。”顾锦屏认为,翻译不是单纯的“文字搬家”,它应当同研究相结合,要深入理解原著的理论内涵,及时吸收理论界最新研究成果,这样才能为理论研究提供可靠的文本依据。
这些年来,顾锦屏参与了《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的译法之争,参与撰写批驳曲解恩格斯晚年思想的文章。他凭借丰富的翻译经验和对原著的深入了解,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相信真理越争越明,他乐见翻译对研究的助推。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奥斯特洛夫斯基借保尔之口说的这段话,被青年顾锦屏奉为座右铭。忆及往昔,顾锦屏释然中也有憧憬:“我的一生没有虚度。如今我年事已高,有些力不从心了,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担落到了中青年肩上。我深信,编译局的这支队伍一定会不断壮大,续写辉煌!”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照片)(本报记者 王琎)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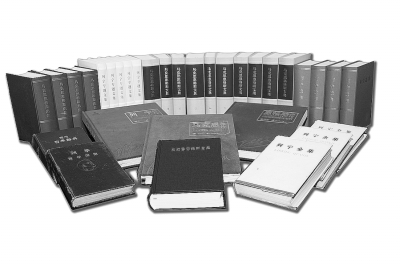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