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届耄耋的王蒙,似乎迎来了又一个创作的高潮期。从《山中有历日》(《人民文学》2012年第6期)、《小胡子爱情变奏曲》(《人民文学》2012年第9期)到《杏语》(《人民文学》2014年第7期)、《你的呼唤使我低下头来》(《上海文学》2014年第9期),风格变幻莫测,令人目不暇接。今年8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推出了长篇小说《闷与狂》,他的这部新作更是将当代长篇小说的艺术形式推向了一个新境界。
王蒙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弄潮儿,是当代小说艺术变革的引领者和探险家,在一定意义上王蒙已成为小说创新的代名词,借用一句流行广告语来形容王蒙的小说创作,就是“不走寻常路”。但《闷与狂》还是在很多方面颠覆了读者的阅读经验。与去年出版的《这边风景》相比,《闷与狂》完全变换了另一套笔墨,表现出了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闷与狂》与其说是一部长篇小说,不如说是一次感觉的狂欢,语言和想象的盛宴,更是一次心灵的自由飞翔,是王蒙的“老来狂”。
在《闷与狂》中,王蒙再一次挑战了小说的“可能性”。与现实叙述相比,小说书写的是一些历史的碎片,是时间的光影,作者将描写的对象从外部经验世界转化为一种生活感受和生命体验。与王蒙既往创作相比,历史的感觉化、事件的印象化、情节的片断化,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显著特点。王蒙曾坦言:“我珍重现实主义,我也倾心于心理独白特别是印象的缤纷。”将一部近30万字的长篇小说完全建立在“心理独白”和“缤纷”的印象之上,在艺术上有极大的难度,这既是王蒙挑战自我的“野心”,更是一次小说艺术的冒险。整体而言,《闷与狂》实现了王蒙“换换小说的写法”的初衷。
王蒙就像是一位印象派大师,在《闷与狂》中把他出色的文学感觉再一次尽情“挥霍”。这部小说完全超越了现实层面“实有”的经验,专注于某种经验之上的更高存在——感觉或印象。故事变成了“潜故事”,情节变成了印象,感觉涨破了语言。感觉成了这部小说唯一的实在。而且,这是一种高度心灵化、诗意化了的感觉,是心灵深处的光焰。与传统的长篇小说相比,《闷与狂》更像是源于作者心底的独语,是一个智者的狂言,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蒙称这部小说的写法为“反小说”。
与王蒙另一部以感觉见长的小说《夜的眼》相比,在《闷与狂》中他对感觉的描写不但没有丝毫的减弱,反而更加饱满充盈,更加激越辉煌。如小说开头对紫藤萝的描写:“如王室的紫气东来,紫而发展变化为白,如玉的深浅浓淡的歇息,如云的层层叠叠的收放,如刺绣的悬挂镶边婉转,如波浪的起伏薄厚开阖,如蟒蛇的藤蔓牵延,如网的枝条伸张,如屋顶的方正齐整,如花毯的巨大平匀,如尘土的切近,如饭食的米香,如花朵的清纯,如水珠的普普通通闪闪烁烁。”王蒙极为推崇托尔斯泰,说他作品里的感觉“简直细致到像工艺品一样”。《闷与狂》的此类描写毫不逊色。
然而,感觉后面仍是小说。在《闷与狂》中,作者剥离的仅仅是故事的外壳,在把故事感觉化、心灵化的同时,则蕴含了更大更密集的信息量。《闷与狂》其实是一部高度浓缩的更加文学化的“王蒙自传”,只不过它呈现的不是生命之“线”,而是生命中的一个个“点”。王蒙说这部小说写的是他的“受想行识”,这是就小说书写的个人层面而言。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说过:“日常生活是每个人的事。”然而,“每个人”的背后,连接的却是一个时代和社会。就宏观层面而言,《闷与狂》指向的仍是一些大主题:青春、爱情和革命。这部小说其实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受想行识”,或者说是20世纪中国的“受想行识”。
《闷与狂》最初的名字叫《烦闷与激情》,无论是“烦闷与激情”还是“闷与狂”,都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两种典型的情感基调和心理状态,也是20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两种典型基调。“闷与狂”,既是对立的,又是相通的,是两种情绪,也是两种文化。《闷与狂》是小说,更是历史;是传记,更是心灵史——既是个人的心灵史,更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这部小说是一代知识分子经验的高度浓缩和印象化呈现,充斥小说的这些片断式感觉不是空泛、无指向的,而是包含着巨大的社会历史内容。在这部小说中,王蒙再一次重新认识自己,理解自己,是作者拉开时间距离后置身其外的一次反观和回味,指向的却是历史和未来。
在美学风格上,《闷与狂》恰如它的书名,也呈现为两极状态,即癫狂与隐晦。它充满了幽默调侃,充满了奇思妙想和智慧箴言,是真正意义上的大狂欢——语言、感觉和智慧的多重狂欢。癫狂,还表现为杂糅的艺术风格,在这部小说中,文体界限彻底消失。可以说,《闷与狂》是小说,也是散文,更是一首抒情长诗;是印象主义大师的画作,更是一部繁复的交响乐。幽默、调侃、反讽、深情兼有,小说、散文、相声、音乐众体具备。与癫狂相对的是隐晦。隐晦造成了这部小说奇异的审美效果,这在当代小说中并不多见。
(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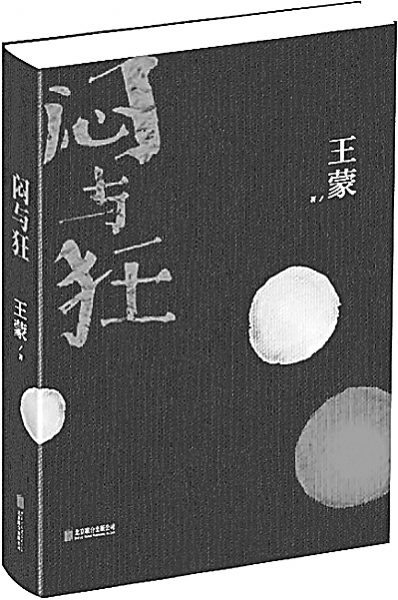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