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梅娘老人走了,一个作家,在2013年5月7日。
我在当天微博发布这则消息时说,老人92岁,但几年前也有学者考证,老人生于1916年11月,这样算来,去世时应该是96岁。梅娘生前对生辰不置可否。对于年龄、身份、职业,对于历史和灾难,对于政治于个人命运的影响等等,梅娘生前从不愿意多说,因为她知道,该来的,一切都会来,该走的,一切都会走。
梅娘老人走了,带走了属于她的一切,没有带走的,是她卓尔不群的理想、母仪足式的情操、拳拳爱国心以及并不算多的文学作品,还有个人日记、书信和对亲友的真挚情谊。
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知道我是梅娘的义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此心存疑惑,且有种种猜测,但我不想再多说什么。这是一段传奇,在中华传统伦理标系不再明晰的今天,而又在梅娘这样思想早已西化且开明的跨世纪作家身上,况且我又人在行伍,促成母子关系的根源如何说得明白!
无从知道梅娘当年为何要认下我这个义子,但在2011年5月8日,她在赠我的《梅娘近作及书简》扉页上写道:“谢谢你对我的感情,这是生命中的珍贵,这是汉文化浸润的两个生命的相知。真的,作为甘愿称儿的你,我非常非常满足,真心地感谢你燃烧了我的暮年。”
关于我和梅娘,老人如下文字竟成了一个作家的绝笔。这或许就是人们说的天意:
钟情于文学的人,都希望自己创作的文字能落实在印刷体上,这是一项真诚的愿望,一项无华的奉献,更是一项心声的袒露。
侯健飞告诉我,他准备出版一册自己的中短篇小说集,这是好事,我举双手赞同。
我与侯健飞的相交,按世况评说:颇有传奇意蕴。
我们天各一方,完全没有相通,是他读了我的书,升起了与我相识相处的愿望,便展开了寻我的行事。经过旷日的找寻,终于“搜寻”到了我,其时我还在受难。
健飞的生母,和我是一个年龄段的女人,在上世纪风云瞬变的时光中,背着自己躲不开的坎坷,用濒死的勇气,拼搏过来,抚育了儿子,自己却含恨而死。这就成了侯健飞挥之不去的心病。他找我,就是想为受难的母亲奉上一颗赤子之心,一颗未来得及献给生母的赤子之心。健飞认为,所有受难的母亲,都应该拥有这样的宝贵。
与健飞长达近二十年的交往,既有文字上的切磋,也有文学中的碰撞,他极尽了为子之责:有什么好吃的,总忘不了我,当我遭遇困难时,他总是及时出现,为我解困纾难,填补了我的丧子之痛。我感谢苍天,赐给我这份亲情。
我没有读过健飞的小说,这是他的有意封存。他忙于编辑,热心于为他人作嫁衣,并乐此不疲。他的近作《回鹿山》出版后,还是我索要,他才送我一本。
健飞的新书,题名为《故乡有约》,故乡之约是人文之本;是不能,不可能不履行的约定。
这是侯健飞的生命之约,是他的风骨。
这是梅娘2012年11月29日写的文字,收在我的小说集里。
文学志趣相投是我和梅娘结缘的基础。其实,我清楚地知道,做人作文梅娘都是不满意我的,就如她总不满意亲生女儿柳青一样。
在过去十几年里,每周或半个月左右,我会去梅娘那里小坐,多半是晚上。我们灯下交谈,谈读书,谈写作,更谈种种家庭琐事——在孩子教育、家长里短方面,梅娘常常“骂”得我坐立不安、无地自容。此时,她手握一支笔,谈到重要的地方,她会把要强调的语句再写一遍给我,这是她多年养成的交流习惯。
我们相聚的时候不算少,但在生活上,我一点儿忙也帮不上,这个独居老人从来不麻烦别人,吃喝拉撒、迎来送往、环境卫生,都是亲力亲为。行走不便时,甚至不让我们扶一把,能上下楼时是这样,不能上下楼时也这样。生命最后一年,她竟坚决地告别了楼下的阳光浴——她不肯让亲友把她背着或者抬下三楼。梅娘活得精致、清爽、有尊严,毕生保持大家闺秀的做派。
二
2002年冬天的某个下午,梅娘打电话让我过去。这情况是少见的,我以为会有特别的事情,但整个晚上,梅娘都在说她父亲和她生母的故事,然后说她自己青年时代的恋情和几个孩子的生死——这是我决然想不到的,这些话题梅娘过去连碰都不会碰一下——关于爱情、女性命运和男人的财富地位,梅娘年轻时只会写成小说。最后,梅娘看了一眼门厅上面一幅俄罗斯少女油画说:“知道我为什么请人临了这幅画吗?”我摇头。“因为她太像我那个死去的二女儿了。淡黄色头发,大大的、微蓝的眼睛……在我劳改时,二女儿得病,没人管,死了,只有14岁……我死了不止一个孩子,这是最让我不能原谅自己的地方,想都不愿意想。我尝过从小没有娘的滋味,也几次尝过母亲失去孩子的滋味!”说到这儿,梅娘突然说:“行了,你走吧,我该休息了。”梅娘常常如此,在她回忆往事时,不愿意有人在旁边,她习惯了一个人承担痛苦。
梅娘去世后,妻子才告诉我,那次是因为她瞒着我,找老人哭诉,说我多次体罚不好好学习的儿子,她不能忍了,准备带着儿子离开这个家。梅娘静静地听着,一个多小时,始终一言不发。直到歇斯底里的妻子突然意识到什么,主动停下来,梅娘仍然没有一句表态的话。送走妻子,梅娘拨通了我的电话。
然而,我同样不能告诉妻子:老人对她这个儿媳也是不满意的。
“你那个来自草原的小海燕,单纯得近于草莽!”“小燕为什么要把头发烫成那个样子?这种发型和她的衣着、气质不搭。”“小燕总是到超市买菜吃吗?为什么不到菜市场买?又新鲜又便宜!”“小燕这样溺爱孩子,早晚是祸,加上你这种大男子主义的粗暴教育,孩子将来哪会有出息!”
当然,关于妻子,梅娘只有和我单独在一起时才表示不满,如果妻子和我一起出现,梅娘总是穿戴整齐,热情上前,拉过妻子的手,把她拉到自己身边坐下,嘘寒问暖,极尽夸赞。每次从国外回来,给妻子的礼物是最讲究的,一条围巾、一对耳坠等等。在我和妻子面前,梅娘对我最爱说的一句话:“得啦,小燕比你更懂得人情世故!”
梅娘对外,看似从容处世,但亲人们都知道,“右派”经历和动荡岁月,让梅娘虽身处安平的日子,却总是堪惊。当年,军人曾是直接执行她劳改的人,而我性情急躁、鲁莽,对上司和工作常有微词,与我相交日久,梅娘就日日担心起我来。有一回她在灯下幽幽地看着我,良久,又良久,然后才叹口气说:“你呀,真是的!要是生在四十年代,在‘反右’和‘文革’里一定会惹上大麻烦……”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当有客人来,梅娘总是把我拽到她身旁坐下。梅娘家那个布面沙发用了很多年,质量很好,布艺换了又换,一年四季干净整洁,我和梅娘并坐在沙发上,常常挨得很紧,能清楚感觉到彼此的体温。
年轻时我喜欢留长发,梅娘有一次问:“这符合军人标准吗?”我知道骗不了这个老人,只好承认,因为自己脑形长得不好,故以长发遮丑。梅娘没说什么,顺手拿起笔,写个纸条递给我:“腹有诗书气自华。”接着,梅娘话锋一转,突然问到我的工资收入,等我答完后,她说:“过去老听说你今天请这个,明天请那个,一个小编辑,这么点儿工资,真够你请客吗?”我懂了梅娘的意思,之前她也曾多次暗示我,国家公务人员,最要紧的是要有公民意识,勤俭节约、廉洁奉公、清白做人,才称得上是国家公务员。
梅娘另一个不满意的人是我的儿子。儿子上初中时的某个春节,梅娘终于同意在我家待两天。除夕之夜,梅娘把压岁钱递给儿子说:“我小时候拿了压岁钱,就盼着街角那个书店早一天开门。买书读书是最幸福的童年经历。”我儿子自幼画画,但却不爱读书,梅娘多次表示忧虑。她接着说:“画画仅凭兴趣哪够!不读群书而画画,不读文学而画画,画到老最多是个匠人,称画家,简直瞎掰!”我和儿子面红耳赤,随后悄悄收起给奶奶显摆的一大叠素描。
儿子画画总算用了心,但文化成绩上不去,失望中我想,或许是“冠男”这名字起大了,儿子哪像个男人中的冠军啊?改名动议了很久,梅娘都不以为然。有一天柳青在场,我又旧话重提,梅娘问:“名字虽然是称呼,也得有意义,你非要改,先说说你喜欢的汉字吧。”我想了一下说喜欢“恕”。梅娘说:“将心比心才是恕,我给你加个‘人’字,什么是人?顶天立地才是人,人最好写,却最难做。克己恕人就是做人的道理。”
2009年,儿子恕人如愿应届考取中央民族大学油画系。第一个学期结束后,他带着自画像去看望梅娘。老人那天非常高兴,满眼都是赞赏的目光。后来老人家在那张自画像上题了“恰同学少年,祝恕人成长”,落款“奶奶梅娘”。临走,梅娘又拦住儿子说:“你必须得减肥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浑身没有骨头全是肉,一点精神气儿都没有。这都是你妈惯的,吃喝起来没个挡……”
现在想起这些小事,历历在目,就像刚刚发生的一样。坦白说来,妻子和儿子都很怕这个老人,柳青姐姐也怕。梅娘敏锐、锋利、明察秋毫。妻子有一天对我儿子说:“你爸是个怪人,没妈非得认个妈,天天骂着。”然而,妻子哪里知道,每次被梅娘“骂”过后,我的身心就会轻松好多天。我们与梅娘老人的思想高度、人生境界,还离得太远,而与梅娘的苦难经历相比,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美好灿烂!
三
但从2012年5月开始,梅娘不再数落我了。因为在那个月,我的左臂出了症状。经过几家大医院会诊,结果都很吓人。梅娘第一时间给国外的柳青打了电话,请她在美国和加拿大联系越洋诊断。
那个晚上,我和梅娘隔着餐桌对坐,一时没有话说。梅娘拉过我的左手,从手腕到手指,正着捏了又捏,翻过来捏了又捏。我的手是冰凉的,而梅娘的手却柔软而温暖……那一刻我真的很悲观。沉默一会儿,梅娘说:“你忘了,一年前我怎么样?生命可以创造奇迹!愁眉苦脸有什么用?!找到病源,积极治疗。”我想起来,2012年春节前,梅娘不幸摔折左膀,高烧入住北大医院,几天后处于昏迷状态,在医院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她竟奇迹般痊愈生还。
那天离开时,梅娘把准备好的一大堆富硒麦芽粉、胶原蛋白营养片和氨基酸整合钙胶囊等让我带走,这些都是柳青从国外买给她的补养品。
以后的日子因为我到处看病,加之柳青也留在国内照顾她,我去看望她的时候少了。但是,只要两周左右不见,梅娘必定打通我的手机了解情况,她甚至学会了发短信。每次见面,梅娘都警惕地观察我的一言一行,以便判断我的状况。为了不让她过分担心,我报喜不报忧,有时故作轻松地开她的玩笑说,您都能活过100岁,我才40多,怎么会死。
转眼2013年春节到了。节前我和妻子来看她,她又认真地问起治疗效果。我笑着说感觉很好。
想不到梅娘突然拉下脸来,正色说道:“健飞,我觉得,你过分了!大半年了,我一直得不到你的真实情况,每次问你,不是闪烁其词,就是嘻嘻哈哈。这种不严肃的态度,你觉得对吗?我们的情分在这里,让我不惦念是不可能的!”
我和妻子一时无言以对,我惭愧得浑身是汗。告别下楼,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在寒风中簌簌地流下来……
四
我终于没有像医院宣判的那样走掉,几个月后,当梅娘楼下那株迎春花刚刚开放的时候,梅娘却走了。
得到梅娘不适住院的消息是两天后的事情了。2013年5月6日上午,我赶到医院时她还很清醒。她躺在床上,旁边是刚刚摘下的氧气面罩。
“怎么样?”她用一贯的口吻问,声音很微弱。我知道她问的是我的病。我说很好。她点点头,看了一眼在阳台上打电话的柳青说:“你告诉柳青,我要回家!”
5月7日早7时许,我在医院大门外一个藏民地摊上买下那个嘎乌——藏民外出背在身上的佛龛,我想以此祈福给梅娘,盼望她渡过难关。
返回病房,发现梅娘戴着氧气面罩,大口喘气,几位医护人员、柳青和邻居好友纪兰英守在一旁。我握住梅娘的右手,是冰凉的。她半睁的双眼转向我,迷离了几秒后忽然亮了一下。她试图用左手摘下面罩,但被护士按住了。
“我要回家……”梅娘冲着我拼尽力气喊出来,这是她最后一次清楚的诉求。
上午9时许,又来了多位医生。他们建议采取切喉插管等抢救措施,柳青却拿不定主意。已经70岁的柳青姐,这些年国内外不停奔波,想尽一切办法照顾妈妈,此时身心憔悴。
10时许,医生说再不采取插管措施就没机会了。柳青一边询问切喉后最好的可能,一边把无助的目光再次投向我和通宵守着梅娘的纪兰英。
又挨过几分钟,非常艰难的几分钟,梅娘每一口呼吸都异常痛苦。我把柳青叫到门外说:“放弃吧!别再受罪了!”说完这句话,我的心像被剜了一刀。但我没有流泪。我给上班的妻子打电话,请她赶过来最后看一眼老人。
10时35分,梅娘停止了呼吸。最后的35分钟,柳青一直趴在妈妈耳边诉说着,讲妈妈的伟大、爱、德行和善良。最后柳青说:“妈妈,我知道您对我们都不满意,但我们知道,您真爱我们;您一生吃了很多苦,都是为我们吃的,我们虽然做得不好,但我们也真的爱您,永远永远爱您!”
一个作家就这样走了,不!在我看来,芸芸众生中,不过是一个有着不凡经历的老人走了。如果说不同,仅仅因为她是一位作家,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作家。但直到今天,一想到竟是我决定了这个老人赴死,心里就异常难过。这是梅娘生前根本想不到的,也是我没有料到的。
妻子赶到时,梅娘遗体已经清理完毕。我和柳青推着永远睡去的梅娘在楼门口与妻子迎面相遇,妻子的表情既震惊又不知所措。在通往太平间的路上,妻子压抑的哭声令人心碎。后来妻子说:“太怪了,本来20分钟的路,竟然遇上大塞车。可能这个婆婆不喜欢我,老天就不让我给她送终。”我安慰妻子:“是不太满意,而不是不喜欢。对子女不满意的父母才是真正的父母,母爱是不会掩饰和虚情假意的。”
在简短的告别仪式上,没有颂歌和悼词,没有领导和记者,来告别的多半是梅娘落难时的难友、邻居和文学挚友——最远的是香港的黄志民夫妇,他们带着一对女儿越洋而来,只为这短暂的告别。而这对女儿芷渊、茵渊从几岁起开始与梅娘老人通信,并有通信集《邂逅相遇》存世。
后事简单得让我一度难过了好久,也许,真正了解母亲的还是女儿。柳青让妈妈一直安静地躺在鲜花丛中,直到入炉那一刻,梅娘身上覆满了水灵灵的百合花。
骨灰被装入汉白玉石盒。从殡仪馆到墓地,需要40多分钟,我有幸一直怀抱着梅娘的骨灰。汉白玉始终是冰冷的,尽管我试图用自己的体温暖热这沉重的石头,重新体会和老人常常并坐时温暖的时刻,然而这冰冷却是现实的、残酷的、无情的,原来,阴阳两界永远不能调和的就是冷暖。
五
梅娘走后,我突然变回从前,像25岁时那样暴躁、易怒、绝情。不会再有一个像梅娘这样的老人数落我、骂我了,我恢复成一个任性的孩子。在商讨出版《梅娘文集》的过程中,有一天我在电话中突然对柳青姐姐大发其火,我说:“以后您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老人走了,把一切都带走了,我们以后不会再有任何联系了。”
放下电话后,我独自哭了,我生气柳青这个姐姐从来认人不准——就在梅娘去世半个月后,柳青认识的一个女记者,以组织派她写梅娘传记的名义,拿着某机关介绍信,到梅娘生前所在单位,拷贝走了梅娘七卷本个人档案。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不可思议,连亲人都不给看一眼的个人档案,而且是梅娘这样一个有特殊经历的人的档案,一个记者,持一封官方介绍信就轻易拷走,事后又矢口否认,意欲何为?梅娘的一生,是多灾多难的一生,更是理解历史、包容历史、宽恕他人的一生,幸好还有梅娘的作品在,我们在看,天地良心在看……
梅娘现在也算团圆了,她和早逝的爱人及4个早逝的儿女同室而居。非常好的墓地,柳青姐选的,十三陵后面的景仰园,依山傍水,安静异常,阳光每天都早早落在墓碑上。快一年了,我一直没有勇气再到墓地去看望梅娘,我想用这篇文章再见她一次,是再次见到,而不是最终告别。我想等到哪一天,在罗马美术学院读研究生的儿子回来,我们一起去墓地。此时我想起来了,梅娘下葬时,儿子抱着奶奶的遗像,当我小心翼翼地把老人的骨灰盒放入墓穴时,我看到站在旁边的他哭了,哭得很伤心,抖动着还很肥胖的肩膀。(作者为出版社编辑,作家,著有长篇散文《回鹿山》和小说集《故乡有约》等)
梅娘(1916—2013),本名孙嘉瑞,出生在海参崴,在长春成长。毕业于吉林省立女子中学。19岁出版《小姐集》。后赴日本求学。22岁出版《第二代》。20世纪40年代先后出版“水族三部曲”《鱼》《蚌》《蟹》。与张爱玲并称“南张北梅”。幼年丧母,少年丧父,青年丧夫,中年丧子丧女。曾被打成“右派”,被迫搁笔20余年。晚年重新提笔,以散文创作为主,出版有《梅娘近作及书简》《邂逅相遇》等。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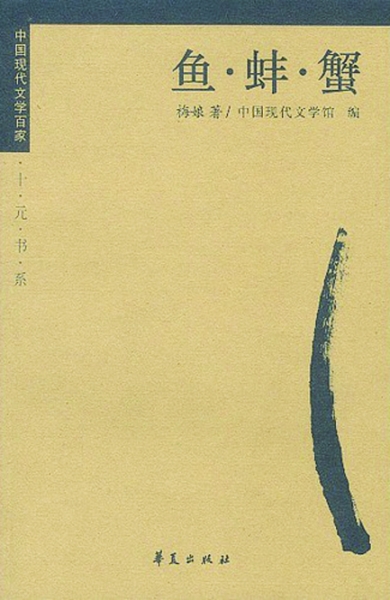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