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革命与军事变革紧密关联的时代,一支军队对科技前沿的认知与把握,已成为一切军事活动的逻辑起点;聚合科技(NBIC),将作为新的“带头学科”重塑未来军事图景——能够对此游刃有余的,才堪任国防“科学技术帅才”。
“八仙”斗不过“船长”
在大科学时代,伴随着科学、技术及工程研发的日趋一体化,国防科技创新领域出现由大科学工程推动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向。
早在19世纪之前,科学仅仅是个人偶发的兴趣或钟情的事业,科学研究乃至技术发明以个体小规模研究为基本特征,人们把这一阶段称为小科学时代。显然,在这样的时代,科技投入不大,政府参与科技创新极少。当时的人们认为,科学与技术仅仅是一种线性关系,即技术由科学决定。但到了20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技术研究和科学研究开始出现规模化的工程特征。如美国的曼哈顿工程、欧洲的尤里卡计划及全球范围的人类基因组计划,都体现了这一变化趋势。美国科学史家普赖斯根据这一趋势,提出了大科学时代的概念。
作为人类总体科技创新大河的一个分支,国防科技创新也经历了从小科学向大科学演进的类似路径。在早期以工匠和发明家为代表的个体创新阶段,武器的主人通常集设计者、研制者、生产者、乃至使用者于一身,其间也有简单的分工协作,但远未形成复杂的社会建制。此时,一件重要新式武器的问世,往往与杰出工程师个人名字连在一起,如机枪与马克沁、TNT炸药与诺贝尔、潜水艇与富尔顿等。当国防科技创新进入国家主导的阶段时,个人发明的痕迹便大大淡化了。莱特兄弟的发明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个发明,它标志着个人发明的结束;坦克的问世则代表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国家主导国防科技创新时代的到来。
伴随着国防科技创新从个体自发的“散兵游勇”式,向国家主导的“联合攻关”式转变,无论是攻关方向的战略选择,研发主体的统筹协调,相关资源的优化配置,抑或是工程项目的综合管理,科研人员的协同创新,等等,都对国防科技创新人才提出新需求:其一,与个体自觉时代的“科学精英”和“发明大王”不同,国家主导时代除了需要群星闪烁之外,还特别需要从群星中脱颖而出的时代骄子——领军型科技帅才;其二,如果说在个体自觉时代,国防科技创新人才重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话,那么,在国家主导时代,国防科技创新人才则需要具备“众人划浆开大船”的协同创新素质。我国的“两弹一星”工程、载人航天工程的实践,都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战争跳出“黑箱”
国防科技创新的“技战融合”,是指传统横亘在军事技术与战争理论之间的鸿沟正在被填平,一方面军事技术内嵌战争理论,另一方面战争理论导引军事技术,这是军事领域的新趋势。如近年来在战场上大出风头的所谓“发射后不管”之精确制导武器,其作战运用就主要不是由战场指挥官掌控,而是由国防科技创新专家在研制时就预先规制的,即用科技手段预先确定其可达到的作战目的。
传统武器装备形成战斗力的一般过程为:预先研究、型号研制、试验生产、列装训练及作战运用。但近年来,网络武器、太空武器及光电武器等新概念武器的试验、训练及作战却出现一体化趋势。以太空武器为例,平时承担太空攻防武器研制任务的科技人员所进行的科研试验,与航天部队开展的任务训练及未来作战,存在着方式、过程及要求的同一性,用专业术语讲,作为国防科技创新“技战融合”趋势的一种具体体现,这些新概念武器出现所谓“试训战一体化”。
从传统的沙盘推演、图上作业、实兵演习,到今天的计算机模拟、实验室推演,借助计算机仿真技术的快速发展,作为行之有效的战争预演实践方式,虚拟演兵日益受到各国重视。战争正在从“黑箱艺术”大步流星地步入“科学技术”的殿堂。现代战争实验室的崛起,正日渐从根本上改变人类认知战争的方式,以往的“经验主导”模式逐渐让位于“理论先行”模式,横亘在传统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古老鸿沟正在消失。
显然,“技战融合”趋势,使过往那种只懂科技研发,而不懂战争理论的国防科技创新人才成为历史的弃儿。相反,一种兼具优良的军事技术素质和扎实的战争理论功底的国防科技创新人才,才会受到时代青睐。
与未来带头学科同行
“带头学科”的概念是苏联科学哲学家凯德洛夫在20世纪70年代初首先提出的。他认为,在过去的人类文明史上,各学科发展并非齐头并进,由于物理学一马当先,同时也带动着其他科学的发展,因而被称为那一个时代的“带头学科”。的确,过去的100年,可以称作是物理学的100年,而由此上溯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也可以称作是物理学独领风骚的历史。从远古人类的钻木取火,到古希腊时期的浮力定律、杠杆原理,以至近代的伽利略实验、开普勒定律、牛顿力学、麦克斯韦方程,一直到现代的相对论革命、量子力学,物理学长期独占鳌头,无限风光,引领着其他学科的发展,影响着社会领域的变迁,同时,也引导着军事领域的变革。
然而,到了20世纪中叶,现代科技发展开始呈现出多方称雄的局面,物理学作为“带头学科”的历史由此终结。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和医学等多学科的齐头并进,开启人们对未来“带头学科”的重新想象与追寻。在人类刚刚跨入新世纪门槛的200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美国商务部(DOC)共同资助50余名科学家执行一个研究计划,旨在弄清哪些学科是新世纪带头学科。由这些科学家研究成果形成的一份报告断言,由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及认知科学聚合而成的全新概念——聚合科技(NBIC),将作为新的“带头学科”重塑未来军事图景。
目前,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已启动一批聚合科技探索项目。尽管对美军有关动向国际军事界存有争议,各国军事发展也不可能拷贝美军的认知及做法,然而其所有关于未来的想象、判断及规划,至少让我们看到,未来的高端国防科技创新人才必须拥有广博的学科基础并了解“带头科学”的前沿动向。
紧盯“带头学科”新嬗变培养高端国防科技创新人才,要求我们对学科未来保持高度敏感,及时更新学科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学科体系是人才培养理念具体落实的路线图。国防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需要依托现有的学科体系,但更需探寻未来的学科动向;“带头学科”就是预知这一走势的风向标。
国防科技创新,本质上是一种智能层面的对抗性较量。率先取得“破坏性创新”的军队,无异于抢占了制胜未来战争的先机;而“带头学科”的每一次新嬗变,都意味一次旧的知识图谱的重组,意味着一轮新的“破坏性创新”浪潮袭来。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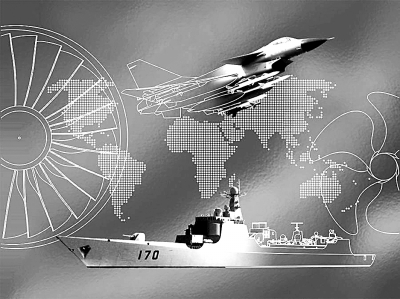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