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是因为鲁国的编年体史书——《春秋》而得名的,以一部书命名一个时代,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唯一的。
春秋并不是政治上最美好的时代,但却是历史上少有的思想自由的时代。伴随着王纲解纽,诸侯自立,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充满生机。春秋士人或效命于战场,或奔走于列国,他们可以敲击着古老的编钟而赋诗断章文采斐然,也可以驾驶着战车而披坚执锐豪气凛然,他们举手投足讲求礼仪,气度从容,赋诗言志,唇齿留香,显示了一个时代特有的风雅精神和君子气韵。雅斯贝尔斯将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时代称之为文化的“轴心时代”,春秋时代正处于这样一个轴心时代里,是整个“轴心时代”文化的动人心魄的一幕。
城邑文明与春秋社会的历史土壤
春秋文化是以城邑文明为历史土壤而生成的,春秋社会变革的核心问题是城邑文明的高度繁荣。
城邑在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指出:“在人类社会史的研究上,城市的初现是当做一项重要的里程碑来看待的。”英国史学家柴尔德(Prof. V. G. Childe)在《远古文化史》一书中指出史前时代有两次重要的革命:一次是新石器时代的工具革命,一次是城市革命,正是有了这样的革命,人类的文明才得以延续和发扬。如果说新石器时代的工具革命标志着人类由蒙昧进入野蛮的话,“城市革命”则标志着人类由野蛮进入文明时代。
侯外庐等学者早就指出,商周时期的文化进步主要因为这一时期进入了“城市国家”。中国不仅有成熟的城邦文明,也有发达的城邦理论与城邦思想。《周礼》每篇都以“惟王建国,辨正方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数语起首,而这正是城邦政治的总体原则。《周礼》是以周代的京畿为中心为诸邦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可供诸邦效仿的城邦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重大影响。我们不仅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座又一座的古城遗址,也在古代典籍里看到古代城邦的理想蓝图。虽然《周礼》不免有想象的成分,但其总体还是以现实为基础勾勒出来的,因为古代中国毕竟有长期城邑文明发展的历史。
春秋时代的中国进入典型的城邦时代。随着周室东迁,诸城邦脱离了西周宗盟的束缚而纷纷自立,走向了独立的城邦时代。
自立的城邦以前所未有的气势聚集着文明聚集着财富聚集着经济与军事实力,诸侯各城邦开疆辟土迅速形成了浪潮。《左传·成公八年》记申公巫臣曰:“夫狡焉而思启封疆以立社稷者,何国蔑有?唯然,故多大国矣。”摆脱了西周盟主束缚的诸城邦不再是甘于小国寡民的旧的城邦贵族,而以一种新的主人的目光打量世界,城邦贵族的自强和自信空前高涨,他们要壮大自己城邦的力量,重建城邦国家的新格局。
《谷梁传·襄公二十九年》谓:“古者天子封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满城以自守也。”而时至春秋,诸侯不再由天子分封,其地也不足以容纳其民,城邑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出来,被焕发出来的不仅是争霸城邦的野心,也有建设城邦的信心。一方面是原有的城邦扩大了增强了,另一方面是旧有的城邑已装不下城邑贵族的勃勃野心,一座座新的城邑建设起来。据清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统计,春秋时期共有都23,邑345,《春秋》与《左传》有关筑城的记载共有66处,这些记载既有旧城的修缮又有新城的建筑,涉及到的城市有82座,由此可见一个以国都为中心以城邑为网络统治着广大乡野的城邑文明系统已经形成。
繁荣的城邑文明是春秋风雅精神的生长的坚实的社会保证和经济支撑。居住于城邦中的是被称为“国人”和“君子”的城市贵族阶层,他们在城市中过着远优于乡野的的富裕生活,享受着城邑中高度发达的礼乐文明。贵族们“紫衣狐裘”(《左传·哀公十七年》),“每食击钟”(《左传·哀公十四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们的居处是“夏屋渠渠”(《诗经·秦风·权舆》),公室是“美仑美奂”(《国语·晋语八》及《礼记·檀弓下》均载)。而外交间往往举行重大的宴享活动,他们于华屋高台间杯觥交错,赋诗唱和,衣袂飘飘,文采风流。这与一般野人的“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诗经·豳风·七月》)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差别。《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在公朝工作的工作餐竟然是“公膳日双鸡”,贵族的富庶与奢华可见一斑。离开城邑文明很难想象春秋风雅精神的生成。
《诗经》与春秋时代风雅精神的文化支撑
清人劳孝舆在《春秋诗话》中将春秋时代的赋诗言志风气概括为“春秋一场大风雅”,《诗经》是礼乐教化的蓝本,其流传的过程是周代礼乐文明不断传播的过程,也是风雅精神在不断深入春秋人精神世界的过程,《诗经》为代表的文化经典是春秋风雅的精神支撑。
1.春秋时代是《诗经》结集和诗歌创作繁荣的时期。
《诗经》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前后结集,从时间上看,收入《诗经》的篇章绝大部分属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时代的作品。《诗经》中春秋时代作品中蕴含着浓重的怀疑精神和忧患意识,不仅数量多,也是《诗经》中思想和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
2.春秋时代是新的风雅精神建立和成熟的时期。
王室东迁,风云激荡,春秋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灵世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与西周人相对平静波澜不惊的心灵世界比起来,春秋人的精神世界波起云诡,笼罩着浓重的迷茫情绪,巨大的悲凉和忧患意识笼罩在春秋诗人们的心头,形成了中国诗人在王朝更替世事兴衰的历史过程中的《黍离》之悲的心灵模式。昔日王室恢弘的宫殿已经是黍稷青青的田野,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引发诗人如醉如噎的心灵悲痛,连脚步也因此变得迟缓而沉重,诗人禁不住追问苍天是谁制造了如此深重的人间苦难?
这是典型的春秋人的心态,忧郁而不平静,苦痛而不绝望,缺少了西周人的凝重矜持,多了几分忧伤和思索。虽然“诗三百”中的忧患意识,仍然不是现代诗歌中毫不遮掩的愤怒,而是有所控制有所保留的在礼乐文化范围内的幽怨,但也表现出一种新的时代气象,使得春秋诗歌有了新的精神格局。《诗经》从西周到春秋的精神变化,被经学家们概括为“变风变雅”,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像经学家那样把春秋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世界描绘成漆黑一团,而应该看到这种失去对天命信仰后的精神忧郁和痛苦,是历史进步过程中的应有的代价。春秋文学表现出来的怀疑、迷茫、牢骚、哀怨,并不仅仅是消极的,而是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先声,比起宗教世界里的盲目的坚定,世俗世界的迷茫也许更有真实的意义。
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
——《小雅·北山》
这是春秋社会宫廷政治生活的真实展现,诗人描绘了种种社会不公,有的人安居家中,有的人为国效忠;有的人躺在床上,有的人在外面奔忙;有的人不知百姓呼号,有的人凄惨操劳;有的人安闲自在,有的人公事繁忙;有的人饮酒狂欢,有的人畏惧祸端;有的人进进出出袖手议论,有的人大事小事竭尽心力。诗人叠用十二个“或”字,排比中有对比,不平之气,蕴积已久,一气呵成,不吐不快,尽管比起所谓“正风正雅”显得的不那么中庸,不那么温柔敦厚,却揭示了世俗世界的种种劳逸不均苦乐不平,具有超越时空的现实主义力量。
春秋时代一种特有的审美精神也在成熟。西周雅颂诗篇中的心灵活动常常是宁静的,宗教的,缺少人间烟火的;而春秋时代的诗歌则是灵动的,世俗的,充满生活情趣的。产生于春秋时代的“变风变雅”标志着从宏大的宗教叙事向写实的世俗描绘的思想转变,也标志着一种审美转向。《诗经》雅颂诗篇中描绘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颂·玄鸟》)的殷商始祖简狄、“载生载育,时维后稷”(《大雅·生民》)的周民族始祖姜嫄以及“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大雅·思齐》)的圣母大姒等非凡女性的形象,这些女性形象是庄重的、崇高的、具有女神色彩的,却是缺少世俗生活情趣的。例如: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大雅·生民》中的姜嫄是周民族带有宗教意义的始祖,生育了周民族的始祖后稷,但是其面貌却是朦胧的,留给我们至多是她模糊的背影。而春秋时代的国风里的诗篇,描绘的则是一批生动的世俗世界里的女性群体。
硕人其颀,衣锦褧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诗经·卫风·硕人》
这位身材高挑,衣着华美的庄姜,拥有“齐侯之子,卫侯之妻”的显赫地位,拥有“邢侯之姨,谭公维私”的贵族身份,但是这样不凡的女性的面貌不再是宗教视野下神圣的朦胧的背影,而是审美世界里的清晰而美丽的艺术形象。雅颂诗篇里伟大的女性往往是生育女神,是一个部族的神圣母亲,而庄姜恰恰是“美而无子”,她的形象不再具有神圣母性的意味,而只具有艺术和审美的意义。诗人赞美庄姜的是她世俗的美丽,像雕塑家一样详细地刻画了她的整体形象——身材修长挺拔,玉手白皙纤长,皮肤鲜亮润泽,脖颈健朗细长,牙齿洁净整齐,蛾眉宛转含情,尤其是她桃花绽放的笑靥和顾盼生辉的双眸,风情万种,春光无限,点睛欲飞,更具有一种动人心魄的风韵。这是一种春秋精神解放下的审美形象,不雕琢,不扭曲,叙述手法是朴素的写实的,塑造的不是女神,而是女人,还有几分迷人性感,是春秋城邦社会土壤上滋养起来的具有崭新意义的审美艺术形象。
3.春秋时代是《诗经》广泛流传渗入社会生活的时期。
赋诗言志是春秋时代独特的文化现象。《汉书·艺文志》谓:“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
称《诗》喻志,可以臧否人物,亦可以观家邦兴亡,意义如此重大,所以春秋时期的诸侯卿大夫都是自幼学诗,从摄职从政的男子到闺阁中的妇女,从中原各国到称为异族的荆蛮、姜戎都练就出触景赋引、应对自如的赋诗本领。据统计,《国语》引诗31处,《左传》引诗219处,这些引诗赋诗活动涉及到宗教祭祀、外交往来、礼仪道德、生活教育等广泛的领域,《诗经》已经全面走进春秋贵族的社会生活。《左传》所记襄公二十七年的垂陇之会,颇有典型意义: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
赋诗者,谙熟“诗三百”的篇章,以诗言志,听诗者微言相感,深解其意。于杯觥交错间,进行深入的思想交流,这样别人看来如坠云里莫名其妙的对话,春秋的赋诗听诗者却进行得行云流水,毫无窒碍,关键是双方对“志”的理解与熟练。晋是春秋大国,郑国这样的小国常仰仗晋国的庇护。晋国重臣赵武出使郑国,国君设宴,七子赋诗,曲意逢迎,赵武喜不自禁,而又借助他人的赋诗转而表达了自己“心乎爱矣”的心志,借他人酒杯,述自己的情怀,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真是赋诗的妙处。
春秋人的确是风雅之至,一方面是钟鼓悠扬,深情赋诗,一方面是妙解其意,因诗“观志”。这是后来任何一个时代未曾有过的诗的时代,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谓:“《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风雅艺术不仅是一种文学分类,更是一种精神气质,在诗的应用中风雅艺术也融入了春秋人的精神世界。
礼乐文化背景下春秋士人的乡党生活
春秋社会一方面表现为礼乐文化的被僭越被曲解被破坏,同时这也是一个礼乐文化被强调被坚持被普及的特殊时代,僭越的是制度层面,普及的是精神层面。春秋士人对礼乐文化的坚持,不仅体现在对宗庙祭祀等重大政治制度的坚持,更体现为一般的日常世俗生活,立足于日常的朴素的乡党的生活。
乡党是周代基础的社会组织,乡里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构成的宗法政治单位。我们不应该用现代乡村的概念理解周代的“乡里”制度,因为周代的“乡”本质上是属于城邑属于城邦的。
乡饮酒礼与乡射礼,是乡党间重要的典礼活动,而整个活动更像一场规模宏大的礼乐艺术的演出,其结构形式具有原始戏剧的形式特征。乡饮酒礼分为迎宾、献宾、宴宾、送宾四个组成部分,正像戏剧的序幕、发展、高潮、尾声一样,这四个组成部分也把普通乡人的世俗生活纳入艺术程序之中。整个艺术过程更像乡党间展演的一幕有长度有主题有情境的恢宏的戏剧,在发生、发展、高潮、结尾艺术地实现乡里之间其乐融融“诗可以群”的现实主题。乡饮酒礼用诗共十九首,乡射礼也以“乐射”为最高境界,乡饮、乡射的过程也是诗乐艺术介入周人世俗生活的过程。
孔子特别强调通过乡党生活建立君子的人格风范。《论语·乡党》的文字多记孔子于乡里间的日常生活形态,把神圣的道德规范付诸日常生活状态的表现。例如:记其衣着是“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记其饮食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记其宴饮是“惟酒无量,不及乱”;记其寝坐是“席不正,不坐”“寝不尸,居不容”;记其乘车是“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乡党》一篇汇集孔子平日周旋动容与其衣服饮食之细,在日常琐屑生活中更见孔子行止之闲雅而合于礼仪规范。《乡党》的最后一节作:
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钱穆先生《论语新解》以为“色斯举矣,翔而后集”当是两句逸诗,由于《乡党》文字多是孔子日常琐细言行,唯恐有“琐屑而拘泥”之嫌,于是以描述鸟儿起落时察言观色的形态起兴,引出“时哉,时哉”的人生议论,使得平凡的生活忽见诗意盎然之情趣,而没有呆板生涩之感。把礼乐精神寓于举手投足之间,将诗意人生引入寻常乡党生活,正体现出孔子歌者之风范。
不唯孔子,诗乐是周代贵族的基本修养,以诗言志,以乐赋情,是通行于周代士人间的风雅之举。《荀子·乐论》谓:“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与钟鼓相比,琴瑟是乡人通行的音乐工具,所以《礼记·曲礼》记:“大夫无故不彻悬,士无故不彻琴瑟。”金属乐器悬于架上,演奏需要诸多条件,非一般士人能力所及;而普通的乡士是要将琴瑟随身携带的。周代的城邑贵族无论是王公大夫还是乡党士人,都有良好的音乐修养,不仅平时琴瑟在身,《礼记·玉藻》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甚至是走路的脚步也要合于音乐的节奏,礼乐艺术雅化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塑造着君子的风雅气度。
道德意义上的君子人格的成熟
“君子”一词在夏商及西周历史文献里已经多有记录,但君子作为一种人格理想却是春秋时代完成的。
君子一词最初的意义是指居住于城邑中的贵族,而不具有道德的意义。《尚书·无逸》谓:“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君子是城邑中“无逸”的人,而小人则是从事稼穑的人,其分工有明显的区别。君子与小人的这种分工的不同是被当时人普遍认同的。《左传·襄公九年》记晋知武子曰:“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君子从事的是劳心勤礼之事,而小人从事的是稼穑农力之事,在他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
君子一词的道德意义是后起的,它经历了从阶级意义到文化意义再到道德意义的转变,而君子道德意义的形成代表了君子人格的真正成熟。当君子与小人成为一种道德的称谓时,它就不是指阶级与阶层的意义,而是指精神的修养了。《左传·成公九年》的一则故事很能反映这一问题:
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其族,对曰:“泠人也。”公曰:“能乐乎?”对曰:“先人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对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问之,对曰:“其为太子也,师保奉之,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不知其它。”公语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太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君盍归之,使合晋楚之成。”公从之,重为之礼,使归求成。
这则故事本身已经具有相当的戏剧性,而更有启发意义的是钟仪在回答景公提问时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精神修养,征服了晋国的君臣,被称为君子,这里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君子人格标准,即信、仁、忠、敏。君子已不是一个人的身份标志,而成为一种道德评价。君子既有从容镇定的外在风范,又有仁信忠敏的内在气质,可以清楚地看出君子作为一种道德评判的标准已经基本完成。后来的中国思想家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构建了以仁为内在要求,以礼为外在风范,以智为文化标准,以勇为英雄气度的君子人格体系。君子的人格标准愈来愈为广大士人所接受,荀子提出了“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道也”的伟大命题,成就君子是中国人一生努力的目标。
压题图片为杏坛设教图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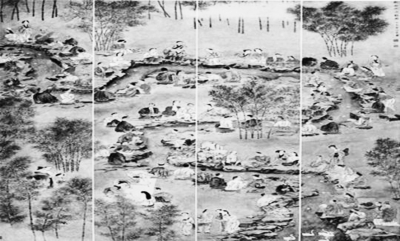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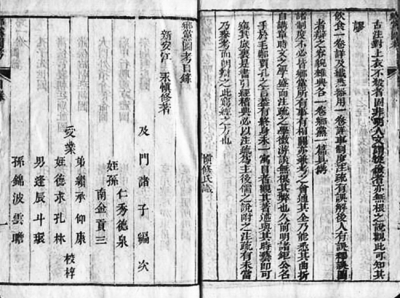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