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薛若琳 地点:北京会议中心
今年是电视历史剧和戏曲历史剧的多产年,早有电视剧《赵氏孤儿》快步登场。为此,我发表一些有关历史剧的感想,希图运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创作历史剧。
一
有论者认为,历史剧发展到今天还在“历史真实”的问题上兜圈子,是历史剧不应有的“困顿”和“徘徊”。其实不然,“历史真实”是历史剧创作绕不开躲不过的核心问题,一百年后谈论的话语还是这个问题,这是历史剧的选择。
历史剧既然是以历史冠名的,那么,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什么是历史?
历史大致由四个部分组成:一是指时间,这个时间是过去的时间,是不可再生的一次性时间;二是指事件,这个事件是已经发生的事件,不可能再重新经历一遍;三是指人物,这些人物是过去岁月中的人物,后世子孙常常把他们置于“缺席”地位;四是指印记,这个印记是后来人的印记,他们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而成为文本。总之,历史是由历史时间、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文本诸多因素综合组成的。
可靠的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它是客观的、真实的;不可靠的是历史文本,它很容易受到历史主观性的支配和左右,从而形成随意性的编织。之所以如此,大约有三种原因:
(一)历史文本的记录者和撰写者往往受到英雄史观的影响,他们只关注一些帝王将相、英雄人物和出众人物,他们对这些人物的撰写又常常采自墓志铭,其实墓志铭中的溢美之辞很多,并不可靠。清代纪晓岚所著的《阅微草堂笔记》就记载一段故事:有个年轻的书生,黄昏行在山中,看见一个岩洞,有一位前辈在那里微笑着向他招手,他大着胆子走进洞中,;因问:老伯并不住在这个地方,怎么独自到此?前辈叹曰:我在世无过失,当了个官没有任何建树,不料几年后,忽然有一天在我的墓前树起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我的名字、官阶,但碑文上所记的事情,是我不曾做过的,有的虽然是我做过的,也夸大其词,游人经过时阅读墓碑,说我不知羞耻,就连鬼物也都嘲笑我,我实在呆不下去了,就避居到这个山洞里。这虽然是一则寓言故事,但它说明墓志铭不可靠,并导致某些历史文本的记录失真。
(二)为了使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生动并具有传奇性,历史文本往往援引私人杂说,例如唐代诗人李白令高力士当场脱靴一事,《旧唐书》和《新唐书》的《李白传》均采用段成式的私家笔记《酉阳杂俎》。其实,当年高力士深受唐明皇的宠信和重用,太子呼之为“二兄”,诸王公贵戚皆呼之为“阿翁”,驸马辈则呼之为“爷”。高力士于天宝初年已封为渤海郡公、骠骑大将军,地位非常显赫。而李白于天宝初年入长安,深知自己的出身是一介布衣,行为比较谨慎,岂能做出那种令高力士脱靴的荒唐事?退一万步说,即使李白当时做了但也不敢讲。那么,到了明皇幸蜀,太子李亨继皇帝位,明皇当了太上皇,赋闲宫中,高力士也彻底失势,状如丧家之犬,当时政治上的一切顾虑都不复存在了,李白本人为什么不讲当年的“英雄壮举”呢?可见此事属于子虚乌有。采自稗官野史、轶闻杂说的历史文本是很多的,就连北宋“奉诏”撰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都不免在该典籍中大量地使用“杂史、琐说、家传”,北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则“喜采小说”,由此可见一斑。
(三)历史文本的记录者和撰写者根据历史人物当时的思想和处境进行揣摩、猜测和主观臆想。例如《左传》鲁僖公二十四年载:在外流亡十九年的晋公子重耳,在秦国的帮助下打回晋国继位,是为晋文公,文公赏赐一批跟随他流亡多年的臣子,介子推跟随晋文公十九年,对文公忠心耿耿,文公却忘了对他封赠,其母让儿子把他的表现对文公讲出来,介子推不愿表功,意欲隐居,他母亲愿与他一起隐去,母子“遂隐而死”。著名学者钱锺书认为:“介子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皆生无旁证,死无对证”,乃是左氏“想当然耳”;“谁闻而述之耶”。其他如某些史籍所载的嫔妃“侍寝”时的“进谗”,这时,一方面是“巫山云雨”,一方面是“枕边私语”,此事极为机密,早把太监宫女打发走了,这些“近侍”都无法知道,史官岂能知之?可见史家在撰写历史文本时,往往采取推测的方法,甚至带有某些文学加工的成分。由于他们主观意识的介入,历史文本的文学性可能增强,而客观真实性可能会降低。因此,在历史剧创作中,我倾向不用“历史真实”的概念,因为这种“真实”是客观的,连史学家在他们的文本中往往都不易做到,还是用“历史史实”较为好些,因为“史实”是史学家笔下的记录,我们一般是沿用这样的记录作为依据来创作历史剧的。
目前,我们普遍认知的历史剧,是由历史和戏剧两种不同性质的样式在特定条件下组合的艺术品种,历史的特点是追求真实性,戏剧的特点是追求假定性,它们处在一个共同体中,必然会产生摩擦、碰撞。于是,在理论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历史剧中历史应当是主体,由它来主导戏剧,引领戏剧,使之成为“历史化”的戏剧;一种意见认为,历史剧中戏剧应当是主体,由它来整合历史,调节历史,使之成为“戏剧化”的历史。
我认为,历史既然进入了戏剧的怀抱,它就应该受到戏剧的调节和整合,使之成为诗意的历史,况且历史进入到戏剧中,常常不是整体的进入,而更多的是以一个或几个个别式的进入,正如郭沫若所说:“拿一分材料,写成十分的历史剧”。
可见,上述两种意见都是针对历史而言的,历史是回避不了的议题。有论者认为历史剧发展到今天还在“历史真实”的问题上兜圈子,是历史剧不应有的“困顿”和“徘徊”。其实不然,建国前和建国后几十年间历史剧的“历史真实”和“文学虚构”的问题,是历史剧创作绕不开躲不过的核心问题,一百年后谈论的话语还是这个问题,这是历史剧的选择。
二
对于革命历史题材来说,应做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但对于一般的古代历史题材来说,应做到“本质不虚,其他不拘”。
近年来,文艺界对历史影视剧和舞台历史剧基本上凝聚了共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这就规范了历史剧的创作原则和写作方法,避免主观随意性的干扰。但是,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内涵和外延仍不甚清楚,给人的印象是,留给剧作家创作空间的只有“小事”才可以“不拘”,然而“大事”可否“不拘”呢?
例如上海京剧院创作演出的《曹操与杨修》,剧中有三个重大事件:“夜梦杀人”、“牵马坠镫”和“鸡肋军机”。它们推动着戏剧矛盾的发展,但是其中两个“大事”即“夜梦杀人”和“牵马坠镫”却是“不拘”而“虚构”的。
又如太原市实验晋剧院创作演出的《傅山进京》,傅山与康熙皇帝“雪天论字”,也是该剧两大事件之一,但这个“大事”也是“不拘”而“虚构”的。这两出历史剧的“大事”虽然属“虚”,但它却折射了历史的可能性,同样具有真实感,所以得到了戏剧界专家和广大观众的认同和好评。
因此,我认为对于革命历史题材来说,应做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因为革命历史题材一般反映真人真事,尤其是涉及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事迹更要慎重。但对于一般的古代历史题材来说,我提出新的虚实意见,即“本质不虚,其他不拘”,因为那段虽然属于真人真事的历史,毕竟比较遥远,距离产生朦胧,但一定要坚持“本质不虚”,这是底线。所谓“本质不虚”,是指在历史剧创作中对历史事件的大框架、大背景不要随意虚构,而对历史人物而言,尽量尊重他们的基本命运(当然合理地改动也可以),尽量尊重他们的人际关系(当然合理地改动也可以),但对其人格的基本定位则要尊重,不能背离,这是“本质不虚”的原则,正如德国剧作家、文艺理论家莱辛所说:“对于作家来说,只有性格是神圣的。”
我们经常听到一个最流行的观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其实,这是一个不准确的概念,一出历史剧既然能达到历史真实(我使用的概念是“历史史实”),为什么就做不到艺术真实?反之,既然能做到艺术真实,又为什么达不到历史真实?何来二者的“统一”?应当指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并不在一个层面上,历史真实在历史剧中属于第一个层级的真实,艺术真实在历史剧中属于第二个层级的真实,它已经融入美学,达到了更概括、更典型的真实。因此,对于历史剧来说,艺术真实是最高的真实。
三
历史剧应当运用历史反映今天的时代精神,把“死历史”变成“活历史”,使历史人物从坟墓中走出来站到今天的舞台上“再度发言”,是历史剧的思想指归。两千多年前有个孤儿,被今天的编导唤醒,拍成电影《赵氏孤儿》,影片对历史尚属规矩,对原著尚属老实,但遗憾的是错过了“再度发言”的机会。
任何一部历史剧都不是为了写历史而写历史,也不是空泛地发思古之幽情,而是现代和过去的对话,是今人和古人的对话,在对话中擦出火花,然后经过沉淀生出戏来。
历史虽然反映的是古代生活,但是剧作家是现代人,他们势必受到现代意识的关照,他们只能以现代的思维来感悟历史,透视历史,用现代思想去激活历史,使历史从沉睡中苏醒,正如黑格尔所说:“这些历史的东西虽然存在,却是在过去存在的,如果他们和现代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关联,它们就不是属于我们的,尽管我们对它们很熟悉……我们自己的民族的过去事物必须和我们现代的情况、生活和存在密切相关,它们才算是属于我们的”。
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奇说:“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他又说:“历史照亮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可见创作历史剧虽然反映的是“历史”,但关照的却是“现在”。
前些时,影片《赵氏孤儿》作为贺岁大片上映,影片是历史题材,它与“历史”有什么关系?它与“现在”有什么联系?很值得我们来探讨一下。
先来谈一谈历史典籍中,关于赵氏一族及其孤儿的命运和这场斗争的性质。
据《左传》宣公二年及《公羊传》、《谷梁传》、《国语》和《吕代春秋》诸书记载,晋灵公是个无道的暴君,他任意杀戮大臣和百姓,晋国臣民对其恨之入骨。大臣赵盾勤勉报国,爱惜民力,深受晋国百姓拥护。赵盾屡谏灵公罢止残暴行为,但灵公不听,反而视其为仇敌,并多次派人刺杀之,幸有义士相助而幸免于难。后来赵盾的同宗赵穿杀死了灵公,赵盾遂立晋宗室黑臀为君,是为晋成公。这场君臣之间的斗争就其本质来讲,乃是体恤百姓的新兴地主阶级与暴虐凶残的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到了成公之子景公时,赵盾已死,赵氏内讧,景公杀了赵氏的一些大臣。这反映了赵氏一门作为新兴的地主阶级并不成熟,是一个不稳定的政治集团。
但是,到了司马迁的《史记》的《赵世家》、《韩世家》中,却出现了景公朝的司寇(一国最高军事长官)屠岸贾,他为了攫取更大的权力,残酷地打击忠臣赵盾之子赵朔,并灭其族。此时赵朔的夫人庄姬公主已怀孕,避居宫中,数月后产下一个婴儿。屠岸贾要绝赵氏的后代,于是搜宫,庄姬将孤儿夹于裙内的袴中,祝曰:“赵氏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此处的“若”字作“你”字解)。“及索,儿竟无声”。程婴是赵朔的友人,赵氏对其厚遇之,于是程婴和退休的中大夫公孙杵臼商议救孤之事,公孙对程婴曰:“立孤与死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于是公孙表示由他去死,程婴担当抚育孤儿的任务,他们找来一个婴儿,由程婴向屠岸贾告密。程婴带着屠岸贾手下的几个将官来到公孙杵臼的家中,不由分说地将公孙杵臼和婴儿一起杀死。这样,孤儿被保护下来。程婴与孤儿藏匿于山中,孤儿就是赵武。景公十五年,景公病重,大臣韩厥把此事的原委和实情尽告景公,这时孤儿已经长大,“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儿”。韩厥逮捕了当年参与杀害婴儿和公孙杵臼的诸将,不久,孤儿率军攻打屠岸贾,“灭其族”。程婴感到事情已经办完,遂自杀,履行他先前发出的在地下见赵盾和公孙杵臼的承诺。
《史记》与《左传》相比,变君臣斗争为臣僚斗争,并且一下子凭空冒出个屠岸贾——恶势力的代表,而且又突然跑出个报仇的赵氏孤儿,程婴与公孙杵臼设计,并冒着风险保护了他,且十五年后,孤儿长大成人,终于灭了屠岸贾一族,报了冤仇。《史记》撰写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就其本质来讲,是阴谋家、野心家屠岸贾与赤心报国的忠臣赵氏一族之间的忠奸斗争。孤儿终于报仇雪恨,标志着正义事业的胜利。
元代著名剧作家纪君祥据《史记·赵世家》改编为杂剧《赵氏孤儿》,但纪君祥对《史记》做了多处异动,其中三处特别重要:(一)《史记》言庄姬生下孤儿,“屠岸贾闻之,索于宫中”,未得,被程婴偷运出宫(详情未记);杂剧谓程婴将婴儿装入药箱冒险带出宫,屠岸贾搜而未得,便张贴榜文下令交出孤儿,如若不交,便将晋国半岁以下的婴儿全部杀死,以斩草除根。(二)《史记》谓程婴与公孙杵臼“谋取他人婴儿负之”;杂剧谓程婴救出孤儿后去找公孙杵臼商议,他提出他妻子近来生下一个婴儿,打算把自己的孩子代替孤儿,请公孙去告发,屠岸贾一定会杀死他和他的孩子,从而使孤儿保留下来。公孙认为自己已七十多岁,时日不多,难以担当扶养孤儿的重任,于是公孙让程婴去告发。屠岸贾率兵来到公孙家中,公孙为了把戏演得逼真,便破口大骂程婴是个贪荣华恋富贵的忘恩负义的小人,又拒不说出孤儿藏匿之处,屠岸贾恼羞成怒,下令军士拷打公孙,屠岸贾为了考验程婴是否与公孙定下“苦肉计”,就命程婴打公孙,程婴为了不被屠岸贾看出破绽,忍痛棍打公孙。正在这时,军士搜出婴儿,屠岸贾用剑将婴儿剁成三段,公孙撞阶身亡。屠岸贾自认为除了后患,夸奖程婴,将其视为心腹,并将程婴的孩子(实为孤儿)认为义子,又令程婴搬进府中做门客。(三)《史记》未言程婴如何“救孤”,只说孤儿十五岁成人,遂灭屠岸其族;杂剧谓孤儿二十岁长大成人,程婴画了赵氏族灭的悲惨遭遇的手卷,元凶便是屠岸贾。孤儿在程婴的指点下仔细观看手卷,悲痛欲绝,他决心要为赵氏先人报仇,并终于雪恨。
杂剧《赵氏孤儿》虽然对《史记》有诸多改动,但它基本上比较符合历史大框架的真实,其人物的人格定位也基本上比较准确。因此,杂剧《赵氏孤儿》仍被学术界认为是一部比较严肃的历史剧。
陈凯歌导演的《赵氏孤儿》中的孤儿长大成人,明白真相之后,终于一剑杀死屠岸贾,为赵氏一门报了仇,孤儿报仇雪恨的人格的基本定位得到回归,韩厥也没有自杀身亡。因此,影片对历史还算比较规矩,其基本情节对原著也算比较老实。而在孤儿亲自杀死屠岸贾的结局上,又超过杂剧《赵氏孤儿》原著,原著是最后在将军魏绛的主持下审理屠岸贾,由魏绛下令杀死这个恶魔的,孤儿只不过是前去逮捕屠岸贾的执行官而已。影片让孤儿直接手刃屠岸贾,实在是大快人心,也是观众的期盼。但是,在以程婴的儿子代替孤儿去死的问题上,影片却兜了一个大圈子:程婴把孤儿用药箱带到家中,妻子埋怨他把祸带回来,在程婴去找公孙杵臼之际,其妻将孤儿作为同庚婴儿交给搜查的军士,她留下的是自己生的儿子。同庚的婴儿都搜齐了,唯独缺孤儿,结果程妻抱着自己的婴儿就自然地被认为是赵氏孤儿了,客观上形成无论怎样解释都说不清楚。当屠岸贾来搜查时,将程婴的儿子当作孤儿摔死,其妻被杀,之后程婴在屠府领回的其妻交出的婴儿却是真正的赵氏孤儿。
影片《赵氏孤儿》的编剧认为,如果程婴按杂剧《赵氏孤儿》中的主动献子以保护真正的孤儿的话,“是反人性的行为”,导演认为,“人会不会主动献出自己的亲生儿子?哪怕是为了救别人,会不会?我觉得难”。编导都一口咬定程婴献子救孤——难。究竟难与不难,我们需要观察和认识春秋时代。这是一个由血亲观念主宰的时代,赵氏的灭族之仇,一定要由他们的血亲家族来报,这符合当时的社会道德规范和行为指归,如果此仇由别人来报是不会被当时的社会接受的,这就是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中,为什么程婴一定要用自己的儿子去死来换取孤儿的生存的春秋时代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现实。况且屠岸贾把全国的一百多个同庚的婴儿都搜进府中,如果搜不出赵氏孤儿,就要屠杀一百多个婴儿,从一对一百多比例来看,程婴忍痛把自己的婴儿交出来顶替赵氏孤儿,从而挽救那么多无辜的幼小生命,无疑是侠义行为。而影片《赵氏孤儿》的编导恰恰缺少文学功力和艺术睿智,他们没有能力把春秋时代的人们的道德标准和行事原则用艺术的方式形象地表现出来,让今天的观众充分地理解,反而认为程婴献子的行为是“反人性的行为”,无非是影片的作者为程婴扣上的一顶大帽子而已。
影片《赵氏孤儿》对这场大悲剧演绎得并不感动人,也不震憾人。赵、屠两个集团的斗争看不出忠奸、善恶的本质所在,而孤儿复仇,也缺少心理准备,只是仓猝上阵,显得苍白无力。程婴“出卖”公孙杵臼,对他所谓的“卖友求荣”(这是春秋时代最无耻的行径)所遭受的社会谴责和心理压力也缺乏深刻的开掘。影片给人的感觉只是匆匆地交待事件,甚至连事件也交待得不够清晰。因此,造成影片《赵氏孤儿》缺乏艺术表现力,难以打动观众的心灵。
今天,影片把两千多年前的孤儿唤醒,使他走到现代的银幕,但这段过去久远的历史,与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究竟有什么联系,也几乎看不出来或无从领略,因此孤儿本可以对今天的观众作强有力的发言,却以自己的平庸失去了“再度发言”的机会。让我们来看看国外学者的论述,克罗奇说:“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室中,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精神有了新出现的成熟,才把他们唤醒……目前,被我们看成编年史的一段一段的历史,目前哑然无声的许多文献是依次被新的生活光辉所扫射,并再度发言的”。
可见任何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一旦进入剧作家的创作视野,他们就会被唤醒,纵跨无数朝代,横穿无数岁月,来到现代的舞台和银幕银屏,虽然演绎着古代的故事,却向观众传达着今天的时代气息,并且评价古往今来的善恶是非和道德准则,启迪今天观众的做人标准和行为规范等等,使历史重新“复活”并“再度发言”,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精神。
影片《赵氏孤儿》对历史的态度,对原著的态度,应该基本肯定,但所缺少的是艺术的感染力和驾驭这段历史的能力,它基本上没有找到“再度”用历史“发言”以及与今天的时代的衔接方式和关注今天的现实的切入点,还没有真正把“死历史”变成“活历史”,这是最大的缺憾。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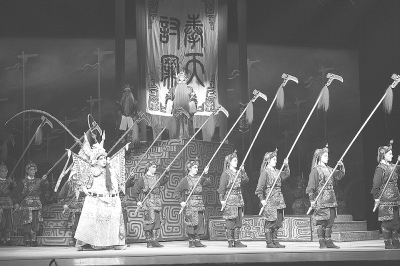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