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装帧雅致的散文集也有着一个同样雅致的名字——《用书铺成的路》。顾名思义,这本文集记录了刘东与书的种种缘分。这些文章中的大部分篇什是刘东为自己写作、翻译或主编的书所撰写的评论与序跋,还有一些围绕个人读书经历、社会阅读传统、学术图书出版等等话题发表的讲演或采访稿等等,而林林总总的话题,都被最前的那篇导引所贯串,并且以作为大写的“人”的作者为主线。正如封面上的那句导读所言,“把这些文字有头有尾地接在一起,就勾勒出了一个关于书与人的很特别的故事”。
和所有爱书人一样,这个故事也照例是从“读书”开始的。刘东是一位从小就对文字着迷的读书种子。无论在“文革”时代一片“读书无用论”的社会舆论中,还是因“黑五类”子女身份而不得不辍学去干又苦又累的翻砂工之时,抑或是在90年代初期经济至上、文人沦为赤贫的社会氛围中,他只要“能独自猫在什么地方,随着性子打开书本”,就一定是乐不可支、兴奋不已的,并且还能随时浮想出各种独创的发挥来。借用作者的话来说——“对于书籍这东西本身,我还算是相当忠实的,甚至可以说,也许再没有别的什么能让我爱得这般永不反悔从一而终”。也正是出于这种对书籍发自内心的亲近和热爱,即便是在经济有些窘迫的时刻,刘东做学术的心情也十分笃定,欣欣然自己能以喜爱的读书为事业,幸运地避开了如今已被钱权“异化”和“分裂”的俗世生活!
当然,刘东与书的故事之所以“特别”,还远不在于上面提及的这些,更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还“意外保有了一种‘创造性转化’的制度遗产,所以竟能以驾驭图书市场为手段,来部分地对抗急速变化的市场化,抵消它在文化方面的短视效应”。作为80年代以来就积极参与种种“丛书编委会”的学人(他曾是“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等极具影响力的丛书的编委),他创造性地继承了这一制度遗产。从80年代末至今,他已经主编了多套丛书,其中包括了在学界业已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至今已22年,选题将近200种)和“人文与社会译丛”(至今已11年,选题已有100多种)。区别于只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化编书行为,作者为自己“设置了一个严明的底线——那就是不管内部阻力如何、外部诱惑又如何,也坚持只推荐最有价值的学术著作”。由此就可以想象,这样的底线带来了需要与各个层面反复磨合协商的众多困难,必得“咬紧牙关”方能“熬成传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中收有几篇为出版遇到障碍的著作所写的荐言,如《保持视界的弹性——为〈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而投书》、《不应叫停,而应道贺——关于李零所译〈房内考〉的出版》等等。这都是今后回顾出版史的好材料。
不过,也正是这些超常的苦功,使得作者读书不再只满足着一己之个人兴趣,“而更有意无意地晕染成一种公共的读书氛围”,并且以出版带动大学学科领域的发展。比如,先出版了洋洋数十种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而后才在此基础上有了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国际汉学”的专业方向。除了这些图书工程以外,刘东还主编具有国际影响的、自负盈亏的民间中文学术期刊《中国学术》,还与专营学术著作的民营书店风入松书店、万圣书园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民间学术界的雏形”,以“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生产模式”来应对“几千年来‘学在官府’的积习和几十年来计划经济的惯性”。
毋庸讳言,对于个人而言,这些编书活动也产生了另一个意外的收获——编书所得成了作者生存的一个辅助手段,使他有可能从经济上解放自己,进而也能更自由随性地发展自己的领域与性情。当然,这意外之获虽肯定是件美事,但正如作者在最近的一篇访谈中所说,“为国家社稷而贪功”才是自己坚持编书的根本动力。事实上,那些单为名利的编书行为注定是短视又短命的,也是绝对不可能“熬成传统”的。
故事说到这里,似乎还没有提到读书人常见的另一项功业——写书。这本书虽也收有几篇刘东为自己著作所写的序言,但数量和所占篇幅却远不及他为编书写下的文字。与所编之书的巨幅目录相比,其私人著述也确乎不算多(大约有三四种,且主要以文集为主)。这是因为他懒惰,或是缺乏才情吗?非也。刘东其实成名甚早,其文与思皆佳的本科论文——《西方的丑学》曾被收入《走向未来》丛书,早早就奠定了他的学术声名。那么,为何他没有乘胜多写几部专著呢?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为他被大量的编书活动占去了时间,但从更深层面来看,这其实与他对于民间学术力量建设的重视和对于个人写作的慎重态度有关。关于前一个原因,前文已经谈及,这里只说说后一个原因。由于反感那些为职称而拼凑、“写得比想得还多”的写作自动主义,刘东宁愿用更多的时间来编书和积累,等到有了足够广泛的阅读和深入的思考,自己也充分自信能够写出像样的文章了,然后再动手写大部头。也许不为很多人知道的是,刘东其实练笔甚勤,撰写的精彩论文不少,常见于各种期刊。只有经过充分沉淀后所撰的著述,才可能含有足够分量的理论创新,以与国内外学界进行深度对话。据笔者所知,随着思力和笔力的步入盛年,写作专著正被逐渐调整为刘东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重心,大约10种书已经被列入了他的写作计划,其中不乏原创性和思辨性极强的哲学著作,而这些书所关注的话题则都是他数十年读书、编书、教书、写文时一直萦绕在心头、已经得到反复思考、急需一吐为快的问题。相信等到这些著作完成,今天介绍的这本《用书铺成的路》又可以再版增容,从而向我们展现一个更加圆满和完整的书与人的特别故事。
需要补充说两句的是,这个故事在今天之所以“特别”,除了主人公才情特异的缘故,其实还有几分因为现今社会的总体风气。说来可悲,在急功近利的现今社会,虽然每年的图书订货会开得红红火火,但真正爱书、懂书的人却越来越少。即便是以读书、写书、编书为业的学术界,在稻粱和职称的召唤下,读书也不再是兴之所至、愉悦身心的精神遨游,而是成了为论文写作而临时赶工的不堪其苦的“有期徒刑”;写书不再是有感而发、水到渠成的“千古之事”,而成了晋升分级、赶鸭子上架的急救篇章;编书也不再是以学术为准绳的学术推介,而成了专以市场和名利为目标的盈利行为。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原本应该是更加正态的书作者与书的故事,反倒显得愈加“特别”了。
由于这本书的文集性质,笔者不可能一一介绍书中文章的内容。关于这个特别故事的种种精彩细节,还要请各位读者自己去细细品读。不过,这里仍有必要提及的是,这本书作者的文章历来用笔讲究、风格独具,所以,即便只从文字本身出发,这本学者散文集也很值得一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
(本文编辑 宋文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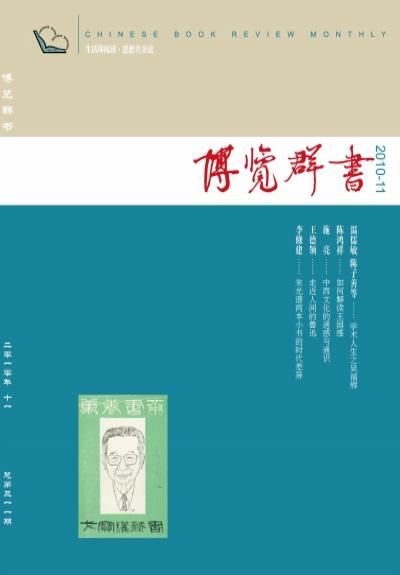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