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当吴福辉兄的大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以下简称《海派小说》)问世时,我就欣喜万分。“海派文学”长期名声不佳,终于有人认真探讨,为之正名了!福辉兄这部大著被列为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之一,当时这个课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明显的学术增长点,《海派小说》是这套丛书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整整15年过去了,海内外的“海派文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海派小说》仍是“海派文学”这个研究领域里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福辉兄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历程颇有意思。他是从沙汀研究和茅盾研究(均可归之于“左翼文学”研究)起步的,而且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他转入“海派文学”研究决非偶然,因为他诞生于上海,始终有一个“海上情结”。《海派小说》后记就说得很清楚:“我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出生地。”福辉兄认为他与上海之间存在着“一份先天的亲情”,因此,“海派文学”研究对于他,“就如同踏上一次返乡的路途”,是在圆他的“一个残缺的梦”!记得有一年,福辉兄来上海,就要我陪同踏访他小时居住的旧宅和求学的虹口中学。他感慨时光的流逝,环境的变迁,与我讨论“海派”研究的多重意义,那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福辉兄主张现代文学史研究者应该“融入自己的研究对象”,他的“海派”研究就做到了这一点。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他读到施蛰存,这是他“遭遇”海派之始,他就觉得“如探入一个新天地”。通过研读施蛰存的作品而进入“海派”,这个选择颇为明智。从初读施蛰存到写出《海派小说》,福辉兄经过了差不多十五六年!在这不算短的时间里,福辉兄埋头旧书刊,爬梳剔抉,抉微发幽,发掘了多少“海派”作家和作品,也逐渐理清了“海派”小说的衍变脉络,从而使他的《海派小说》坚持从当时的具体语境出发,坚持从文本出发,对“海派”文学进行新的历史考察,言之有物,不发空论。
且不论福辉兄对30年代“京海之争”的回顾评论如何持平中肯,他对海派小说文化风貌的剖析就令人耳目一新。他讨论的“海派”作家真多,张资平、刘呐鸥、章克标、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林微音、黑婴、禾金、予且、苏青、徐訏、令狐彗,直到张爱玲、东方蝃蝀等等。尽管这些作家的小说成就有高有低,文坛影响有大有小,但他们如何各自在人的主题尤其“现代人性”的文学表现上进行开掘、如何各自在小说文体先锋性上进行实验、如何各自在大众趣味和开放姿态的结合上进行探索,福辉兄对此都作了细致而又独到的分析,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肯定。其中有好几位,若不是福辉兄提出并加以评论,恐怕至今仍尘封于浩如烟海的旧报刊中。
《海派小说》之后,福辉兄再接再厉,继续撰写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中直接、间接涉及“海派文学”的章节,出版了《京海晚眺》和《游走双城》两书,直至最近推出集大成的专著《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以下简称《发展史》),他的“海派文学”研究得以不断拓展和深化。归纳起来,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据我所知,福辉兄率先提出研究“海派”必须重视海上小报的研究。在他悉心指导下,李楠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福辉兄在为论文单行本所作的序里指出“上海小报是现代都市中下市民的文化读物,前后经历了晚清暴露和狭邪文化、民国鸳蝴文化与海派通俗文化三个时期,这正是现代中国市民文化的三种成份”。他强调“上海不是一个平面的都市,仅从小报的切入便够让人目眩”。海上小报文学“有自己的与纯文学基本精神相通而不尽相同的评价标准”。因此,研究“海派文学”必须触及小报,研究小报,否则,那将是一个重大的缺陷。有些论者对研究小报持否定态度,实在是皮相之见。也正是基于此,5年前他与李楠一起在上海小报《小日报》上发掘了张爱玲的中篇小说《郁金香》,这是近年张爱玲研究的一个了不起的发现。我有幸参与鉴定小说真伪的全过程,亲眼目睹了福辉兄作为一位文学史家的慎重和周密。
其次,又是福辉兄,在新时期以来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率先重提“海派文学”中存在一个“张派”,虽然他自己并没有这样明确表述。在《海派小说》中,他就态度鲜明地指出:“海派以张爱玲为最高代表。”到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他一方面进一步肯定张爱玲的小说“使得现代小说有了贴近新市民的文本,既是通俗的,又是先锋的,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是中国文化调教出来足以面对世界的”;另一方面评论了几乎被遗忘的东方蝃蝀,认为他以“一册《绅士淑女图》,用一种富丽的文字写出十里洋场上旧家族的失落和新的精神家园的难以寻觅,文体雅俗融洽,逼似张爱玲,透出一股繁华中的荒凉况味。东方蝃蝀小说在意象的选择和营造方面,也和张爱玲一样与现代主义相通”。这不仅是东方蝃蝀首次进入文学史著述,也指明了东方蝃蝀属于“张派”作家的事实,从而与半个世纪前王兰儿提出海上文坛客观上存在一个“张派”的观点遥相呼应。
第三,也是更为重要的,福辉兄在长期研究“海派文学”和现代文学史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程的新的总体看法。他在《发展史》中自觉地寻求文学史的多元阐释,提出中国现代文学在30年代以后形成了“多种的文学形态,基本的是左翼文学、通俗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这四种。哪一种在哪一个阶段都没有独霸天下,各自有各自的读者群体,分属于政治文学、商业文学、纯文学这三种文学系统。系统之间也不隔着千山万水,而是相互撞击、转化”。这个观点渗透于他这部文学史专著的始终。福辉兄这种新的中国现代文学格局观的提出,既表明福辉兄作为一个文学史家对阐释历史的新的追求,也表明他对“海派文学”的认知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事实上,他一直力图通过这四种文学形态错综复杂的关系,尤其是“海派”与“京派”的冲突和对比中来讨论“海派文学”的消长,来评判“海派文学”的成就和局限,只不过在《发展史》中表现得更为清晰、更为全面和更为成熟了。
福辉兄赠我《发展史》时说过,我们都是搞文学史的,应该对文学史有与前人不同的梳理,这本《发展史》就是他的一个尝试。确实,新时期30年来,以个人之力独立完成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的毕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福辉兄无论在宏观把握还是微观研究上都可谓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令我钦佩。当然,文学史家应该保持清醒,文学史家往往会出现这样的偏差,即研究一位作家或一个文学流派久了就会被研究对象牵着鼻子走。我想福辉兄一定对此有足够的警惕。以福辉兄研究“海派文学”的建树和积累,我期待他再次“融入研究对象”,扩大研究范围,再写一部新的更为翔实厚重的《海派文学史》。
(本文编辑 荣方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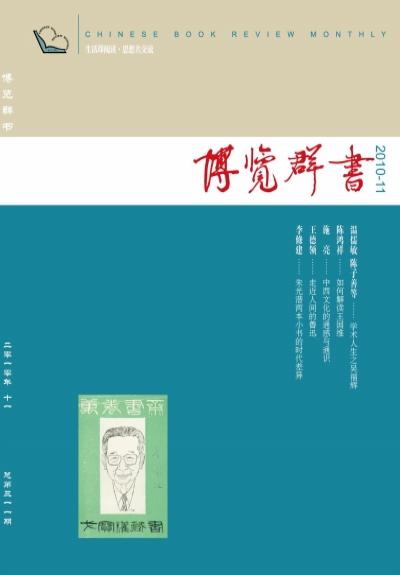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