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单独一人,短短一生,在历史的漫漫长河和汹涌波涛中,几乎不可见。无论伟人还是平民,一律逃不过时代的影响,也一律折射出时代的特色。尤利乌斯·伏契克也一样。他活在时代的风口浪尖,随着风向,他被褒上天堂,又被贬入地狱,显示出历史的极不公平。近年来,我数次去布拉格,从岁月尘埃中寻访他的足迹,发现他既非神灵亦决非魔鬼,而是一个血肉饱满的真正的人,一个可敬可爱的、为时代作出了贡献的人。我从有关他的著作文章中摘录出他人生中的七个片断,以飨读者。
“从门口到窗户七步,从窗户到门口七步。”七,概括了他的一生。
1910年:童年的舞台
7岁的尤尔恰·伏契克,斯米霍夫剧院年纪最小的演员,出色地获得了观众们的认可,他在《蝙蝠》、《多勒尔的新娘》、《地狱里的教授先生》等小型歌剧中的表演尤其受欢迎。在上期提到的摩尔的歌剧中,尤尔恰出演来自天堂的信使,他对于这个角色的塑造正如台词一般:“马蒂斯卡,我觉得这般不寻常!”可以预言,尤尔恰在戏剧领域将大有所为:他早就不是那个初次担当孩童角色的三岁小孩了。此外还有必要提个醒,他身上流着艺术家的血:他的父亲是施万达剧院合唱团的主要成员,而他的叔父是倍受喜爱的著名指挥家、作曲家尤利乌斯·伏契克,不久前我们才刊登过他的照片。(《尤尔恰·伏契克》,《图刊:布拉格-布尔诺》,1910年4月2日)
1918年:少年的思考
“街对面住着个工人。社会民主党人。我叫醒了他。他很快在床边套上衣服。他想知道更确切的消息,问个不停。自由?是吗?独立?是吗?谁?是谁宣布的?是谁领导的?
“我认为关键并不在于此。他不信任那些实现了这一壮举的人们,这伤害了我。他挑战式地激动地对我说:我们得从中搞清楚,这新自由到底是带给谁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没能领会!这对我来说有些可笑。担心这个!明摆着,是带给我们的自由,给我们所有人,不然还能给谁?
“他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耸了耸肩。
“我又如何能忘记他呢?这个在1918年10月28日午夜就已率先看穿了的人。”(伏契克,《回忆起……》,《创造》杂志,1933年11月2日)
一战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于1918年10月28日宣布独立。请留意,其时,伏契克15岁。
1928年:表达的权利
于是我们就动身了——约瑟夫·霍拉、伏契克和我——去拜访沙尔达。他那时候住在维诺赫拉德区的运河街。我们三个都早已熟识沙尔达了,不过霍拉和我两个还是觉得这个计划有点过于大胆,在前往维诺赫拉德的路上我们跟伏契克谈起这种感觉。伏契克只是笑笑。他喜欢冒险,就算出了什么岔子,也不会放在心上。
我们走进沙尔达的那间布置着庞大书橱、笼罩着学术安静气氛的工作室,此时我们感到这计划无比荒唐——我们要拉沙尔达做的事,只能给他带来麻烦,把武器交到他敌人的手里。
伏契克开始说起来,我俩则尽量附和。“这些事情我清楚,”沙尔达说。沙尔达喜欢听伏契克讲述。在以前的多次拜访中,伏契克总是要激怒他,要跟他铺开谈论社会理论并且说服他。沙尔达喜欢伏契克的热情,不过他总是会插上几句讥讽意见,试图把伏契克逼入窘境。这是尖锐而又有趣的游戏。沙尔达慢慢完成热身,接下来争论就会进行得飞快。但这一次沙尔达沉默着,显得有点过于严肃冷淡。
“好吧,”沙尔达终于说,“就算我同意你们的提议,但我还是得继续担任杂志的所有人和责任编辑。要不然他们还是会把你们的杂志给查封。”
“是的。”伏契克回答说。
“而我实际上是不能干涉编辑部的事情,是不是?你们登你们想登的东西,他们则追究我的责任,把我关起来,是不是?”
“这种事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出现了难以忍受的安静。伏契克沉默着,我们也沉默着。
“知道么,”沙尔达终于说,“正因为如此我要干。我还没听说过会逮捕大学教授,我也想试试看。”(作家伊日·维伊尔,《回忆尤利乌斯·伏契克》,1947年)
弗朗基谢克·夏维尔·沙尔达(1867-1937),文艺批评家,伏契克在查理大学哲学系旁听时的老师之一。1928年捷共机关报《红色权利报》遭查禁后,伏契克从沙尔达那里要来了由这位前辈主编的《创造》,把它从小范围内的纯文艺刊物改造成文学和政治混杂的大众刊物。
1939年:给未来的信
彼得内克,两个晚上我在工作和隐隐的激动中通宵未眠,第三晚我又焦虑不安无法入睡。我因你而不安。我闭上眼睛,想像着你:你如何出生,长大,发育成熟,变成男子汉……有一天你提出了一个问题。我知道,必然会这样的。我在自己床上无力地辗转反侧,因为我害怕你也许无法理解。是的,我知道:这问题已经在你心头积压数年,总有一天它将冲破你内心对父辈的尊敬和友谊,你会问:那时是什么样的?怎么能像那样?似乎那都是非常久远的事情了。然而你会说:可是我的父母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啊。他们怎么能生活?他们怎么能默默地承受那降临到人头上的痛苦屈辱?他们又如何能去爱?那时候奴役和屠杀在欧洲大地上阔步。正义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贬低。任何跪着求来的面包都必然味道辛酸。他们怎么能忍受?他们又做了些什么来抗议反对?他们认识到这些么?他们感受到这些么?那该是些怎样古怪、怎样难以理解、怎样非人的人类啊!他们身体里流淌的是人的血液么?他们拥有人的神经么?他们有人的心么?他们到底还是不是人?
……
但谁知道,我们是否能见面呢?我因此而写。我的文字仿佛封在漂流瓶中的信息,我把它抛进时间的海洋,但愿幸运的海浪会将它带到你的脚边,请你擦去蒙在我们激情上的霉斑,读一读关于我们这辈人的文字吧。但愿你能理解我们,我亲近而又陌生的孩子。
我的彼得!(伏契克,未完成自传体小说《彼得的上一代》序言,1939年3月16日)
1938年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划归德国。1939年3月15日,德军开进布拉格,捷克沦为捷克与摩拉维亚保护国,斯洛伐克独立,成为德国控制下的卫星国。
1942:“高水准的戏”
1942年2月18日或19日,按照事先约定,我和齐卡在维谢赫拉德火车站的街对面碰头。我从河边过去,看到奇卡和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一起过来。……齐卡把陌生人介绍给我:这是我们的朋友贝兰。
齐卡对我说,这位朋友想就知识分子的事情和我谈一谈。我、齐卡和贝兰开始朝维谢赫拉德方向走去。此间贝兰就知识分子小组问了我若干问题。
……
这里我必须给针对我的调查插入一个重要注释。在我、贝兰和齐卡的这次碰头中,还谈到了下次碰头的方式和时间问题。齐卡建议说,最好能把碰头方式定下来。他对贝兰说,秋天的时候,他跟我约定了一种碰头方案,后来证明也很好用:每个月17日和21日的17点和21点在布拉格的波多利区的17路和21路电车车站碰头。齐卡接着说,这个约定很不错,他跟我都从没有忘记过……我、齐卡和贝兰的这次会面有一部分进行得很不顺利。我们又谈了一会儿无关紧要的事情,贝兰忽然提出,这个17和21的碰头方式很不错。他问齐卡是否准备好执行这个约定。齐卡回答说是,于是他和贝兰就这么决定了。贝兰对齐卡说,最好也把这个碰头地点告诉那些和摩拉维亚的联络人。齐卡答应贝兰说他会告诉摩拉维亚的联络人。在他们商谈的时候,我离得稍有些远,因为我与齐卡和贝兰之间的这个商谈没有什么关系。(伏契克,在盖世太保那里的口供,1942年6月29日,1954年6月作为苏军在柏林的战利品由苏联交还捷克斯洛伐克)
我和伏契克一起去布拉尼克参加碰头,大概去了五次。每一次我都必须向莱梅尔递交书面声明。我很清楚,这些碰头不可能是真的,因为它们是部分由我、部分由伏契克编造出来的。每个月17日和21日我们都和两或三个职员一起去布拉尼克。……我自己总是和伏契克一起坐在碰头地点附近的某个甜品店或者饭馆里。职员们在外面注意情况,而我总是和伏契克谈起军事和政治形势。等了大约一个小时后,我就托辞说还得和伏契克一起出个公差,把职员们打发走。这里我必须提一下,和伏契克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常常谈起布拉格和它的遗迹。我从这些谈话中看出,伏契克爱布拉格超过一切。我也曾非常喜欢布拉格,就一直和他讲自己在布拉格工作时的事。我还告诉了他一些布拉格在一战期间的小细节。等职员们离开碰头地点乘电车走了之后,我就和伏契克一起登上事先准备好的公务小汽车,顺着伏尔塔瓦河行驶,经过查理大桥,沿着聂鲁达大街开上城堡区。在城堡前我再找个借口把司机打发到某条偏巷去。然后我自己就和伏契克站在布拉格城堡前的斜坡上,久久地俯视布拉格。某几次都已经到了晚上22点,就算这么晚了我们仍然要看会儿布拉格。有许多次我们站在斜坡上超过一个小时。我和伏契克也常常走进圣维特主教堂,看看某些景点。然后伏契克就会告诉我一些关于这个景点的有趣故事。有一次我和伏契克一起走下城堡前的阶梯,直到聂鲁达大街上我们才登上汽车。(约瑟夫·博姆,在捷克斯洛伐克侦查人员那里的口供之一:《尤利乌斯·伏契克及其同伙》,1946年5月)
根据来自捷共中央的决定,《报告》结尾处与这场“高水准的戏”相关的段落从1945年的第一版开始就被删除,20世纪60年代,很可能是在看到了部分相关档案后,伏契克的遗孀古斯塔决定要出版全本的《报告》,然而这计划直到她去世也未能实现。
1953: 命运的漩涡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伏契克崇拜全面到来。这是苏联阵营(包括捷共)对斯大林和其他“低层些”的共产主义运动人士崇拜的巅峰时代(同样也是斯大林力量的巅峰);这是政治审判的时代,其目标甚至也包括苏联阵营的许多主要代言人;这是冷战加剧、为预计中的世界大战作准备的时代。当时竭尽可能地培养对伏契克的钦佩,参与者包括政治家、诗人、青年团员、教师,直至专业干部,影响人们思维的最有力工具也被加入其中。真正的顶点大致出现在1953年,即伏契克被害十周年(殉道的时刻自然非常重要)和诞辰五十周年。
古斯塔在这一年公布,有一万八千人成为了伏契克勋章的新持有者(此活动自1949年就开始实行)。五十年代初,她虽然声称不应将伏契克想象为“某种传奇”直至“非人”的人物,但同时自己又贡献了最常被使用的颂歌,实际上却是些慷慨激昂的空话。在这段时期以及接下去的年代里,《绞刑架下的报告》获得了最广泛的传播,扩大到东方和西方的许多国家(西方主要是在左翼圈子里)。对它的诠释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针,并与对资本主义发起“最后进攻”的想法联合在一起。
就在同时,出现了针对伏契克怪诞的、至今也无法完全解释清楚的安全审查。1952到1953年间,国家安全局传唤了许多与伏契克和知识分子民族革命委员会相关的人。事实上更早就有这回事,战后不久和五十年代初,地方安全局和国家安全局的某些工作人员——这或许也是某些政党和政治力量间斗争的反映——努力让讯问不仅仅关于伏契克,而且也“针对伏契克”(也就是说:反对他)。约瑟夫·博姆自己也觉察到了这一点——他的某些口供也显示出他对此有所觉察。在对知名的捷克籍盖世太保员工(如帕能卡、斯莫拉、贝尔卡等)的审问中也可以发现不少猜疑。其中某些东西后来在安全部门的职工圈子里作为重大秘密私下传播,并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对《报告》真实性的另一怀疑源头。(弗朗基谢克·雅纳切克,《怀疑与肯定》,1995)
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审判波及甚广,遭到灭顶之灾的既包括民主人士米拉达·霍拉科娃(1901-1950),也包括原先的捷共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1901-1952),伏契克在《红色权利报》和《创造》杂志的同事扎维什·卡兰德拉(1902-1950),以及他和古斯塔的证婚人贝德日赫·莱岑(1911-1952)。
2010 :盖棺未定论
2010年7月,捷克科学院捷克文学所的帕维尔·雅纳切克,1995年《绞刑架下的报告》评注版第一作者的儿子,把我领进民族剧院附近一家藏在小巷中的小酒馆。我们坐下来。他把目光停在贴着颜色鲜明海报、灰泥有些开裂脱落、装着深色木头护板的墙壁上说:这才是他年轻时和朋友同事一同来聊天的酒吧,布拉格味道的酒吧。他给自己要了一杯啤酒,给我要了一份从没听说过名字的饮料,说:这个你在给游客开的饭店里可看不到。
然后我们开始谈正题。
1995年的评注版提到将要单独出版伏契克自己在《报告》里提到的口供、针对他那一伙人的起诉书、捷克知识分子民族革命委员会的相关档案材料等:“将呈现某些著名文化代表人物的最后时候,同样也将呈现站在德国警察那边的对手们的供词,呈现他们为重建祖国、为争取生活和文化自由而斗争的证据。”15年了,这些材料现在在哪里?
好吧。
天鹅绒革命之后,帕维尔的父亲、受布拉格之春事件影响的弗朗基谢克·雅纳切克,从斯柯达集团档案部门重回二战史研究单位,他和历史学家阿伦娜·哈伊科娃(雅纳切克和哈伊科娃许久以来一直保持着合作关系,1989年前,某些合作作品只能顶着哈伊科娃的名字发表)、工人运动博物馆的馆长莉布谢·艾莉阿绍娃一起,坐下来花一天时间阅读了古斯塔生前一直不肯公开的《报告》手稿原件,定下了要出版评注版《报告》的计划。在联合了更多专业人员进行长达五年的研究后,1995年评注版问世。同年12月,弗朗基谢克·雅纳切克辞世,留下一大堆按照个人风格整理排列的档案、访谈纪录、文献、笔记,关于伏契克的那部分到了儿子帕维尔手上,剩下的交给了国家档案馆。由于没有合适的人员顶上弗朗基谢克·雅纳切克的位置,计划中的第二本书一直没有出现。如今阿伦娜·哈伊科娃身体状况不佳,在精神上更是受到弥漫在捷克的反共宣传和情绪的影响,已然许久没有和外界联系了。按照弗朗基谢克的遗孀、捷克文学研究专家雅罗斯拉娃·雅纳奇科娃的说法:共产主义对于她来说是,信仰。
然而2008年捷克文学所召开了为期两天的专题会议《尤列克·伏契克——一直活着!》,会议论文集的出版工作正在进行中。所有167页手稿也在2008年的第40版《报告》中公开。捷克年轻的历史学者开始对弗朗基谢克·雅纳切克遗留下来的个人档案进行整理发掘,按照帕维尔的说法:也许会取得重要进展,就在今年秋天。
即使在民间仍然将伏契克作为前政权片面宣传、竭力鼓吹的代表人物来反对,流传着什么他是盖世太保的密探、没有被处决而是溜到了南美之类的传言,但那些具有认为“历史应当为人服务,但绝不是任人驱使”的头脑的人士,确实在努力重新发掘历史真相。尽管速度缓慢,但早已上路。
注:文中除书籍封面外的所有图片版权属于捷克共和国工人运动博物馆(Labor Movement Museum),请勿转载他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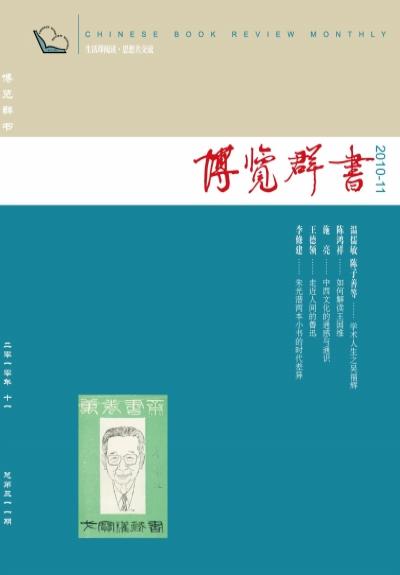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