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朱正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11月版,29.80元
近一百年来,鲁迅一直处在论争的位置上,在他身上,寄托了许多积弱的中国人太多的奢望。鲁迅和民族、国家、革命等巨大的字眼紧密相连,鲁迅研究早已成为显学,有关鲁迅的传记,也有了许多本。作为一个作家来说,鲁迅被过度关注了,也被过分扭曲了,“鲁迅”已经演化为承载中国意识形态的一个特殊的载体,而一个真实的鲁迅往往被遮蔽了。
鲁迅被意识形态化的原因很多,有不少研究者把原因主要归结为由于中国近现代政治文化从外围所作的空前挤压,由于意识形态的刻意“塑造”、“扭曲”,而形成了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鲁迅。我认为,鲁迅的意识形态化,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来自鲁迅本身。鲁迅和他所处的时代靠得太近,他生前的文艺生活充满了论争,除了翻译和文学史研究,他写下的大多数是论争文字,就是他的一些小说,也时时埋伏着影射、回击论敌的文字。他留下的文字,远非静穆、悠远之作,倒是充满了杀伐之声。日本学者竹内好认为,“把十八年的岁月消磨在论争里的作家,即使在中国也是不多见的。”(《近代的超克》,(日)竹内好著,孙歌编,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三联书店2005年3月版,P4)由于致力于论争,鲁迅常常处在不同的政治态度、思想文化的交锋中,鲁迅所处的文学场域激流湍急,给人的印象难免不是意识形态化的。问题是,鲁迅的这种文化立场,一旦和左翼文学有了相同之处,被纳入到国家、民族解放等话语体系中,就非常容易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利用、操控,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了。这样,有关鲁迅的一切就迅速变形,里面的鲜活成分被榨干,成为本质化的宏大叙事。
如何把鲁迅从一个过分偶像化的神,还原成一个人?我认为,剥离开几十年来政治意识形态反复涂抹在鲁迅身上的各种装饰,露出本原面目,是新世纪的鲁迅传记写作所要着力解决的。当然,对本原面目的还原是一个奢望,不仅因为一个鲜活的鲁迅,早已经在1936年逝去,而且,对于历史人物,我们永远难以还原本来面目。我们所要做的,是逐渐走近一个真实的鲁迅,一个正常的人间鲁迅。
鲁迅传记不好写,因为鲁迅往往和革命、启蒙、反封建等20世纪中国的宏大叙事联系在一起,往往把鲁迅作为国家、民族叙事的一部分,把他作为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的代表,作为反封建的启蒙者和英雄。事实上,许多鲁迅传记,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写下来的。作为一个血肉之躯,鲁迅当然也有七情六欲,也食人间烟火,有优点,也有缺点,并非全人。鲁迅有伟大之处,也有偏颇的地方,譬如他对中医的极端态度。如何跳出以往的意识形态的偏狭视角,尽量写出一个真实的鲁迅,是鲁迅传记写作中的难点。
朱正先生的《一个人的呐喊》不以观点见长,而以材料取胜,强调论从史出。这样说并不是否定朱正先生的这本传记在见识上的欠缺,而是说,朱正先生治学的严谨与精审。正如王得后所言,此书“语必征实,史料丰赡,考证精审,知人论世,特立不群”。朱正先生不仅对鲁迅的一生极为熟悉,对鲁迅作品的解读也比较到位,而且对鲁迅先生的周边,大至时代,细至亲人、友人、政敌等,皆如数家珍,娓娓到来,语调平和,持论公允。世上多的是夸夸其谈、无中生有的传记,《一个人的呐喊》如此在厚实的史料基础上治学,自然会得出许多无可置辩的结论来。况且,朱正先生在材料运用上,在追求准确性的前提下,尽量采用近年才出现的材料。因此,许多章节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透过所谓的宏大叙述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朱正先生寻到了一些裂隙,使原先定为一尊的可靠叙述变得不确定起来。譬如,该书的第十八章《“新生活”》,叙述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组建新家庭的生活。朱先生在鲁迅给韦素园的信中,发现了鲁迅对自己和许广平的结合流露出的一些犹疑和彷徨。为此,朱先生质疑道:
写这封信的时候,距他们的儿子海婴9月26日出生,只有半年时间了。为什么还要说“难于‘十分肯定’”呢,还有什么要“且听下回分解”呢?对于“新生活”为什么“很想变换变换”呢?这些文字所包含的是怎样的具体内容,当然是已经无从猜测了。但是这些文字所流露出来的情绪都是十分明白的。读者可以认为,至少在鲁迅写这封信的前后,他们之间出现了某种“难于十分肯定”的因素。
可见,二人在上海的同居生活未必都是相敬如宾的,之间的小摩擦或者是小麻烦肯定是存在的。这一点同样可以在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写过的一篇《〈鲁迅年谱〉的经过》中找到佐证。
另外,朱正还引用楼适夷1973年7月11日写给黄源的信,以证明鲁迅其实是不愿许广平参加社会活动的:
因先生在世之日,是不大愿意让许参加对外活动的。许在沪曾参加过国民党市党部办的妇女刊物,是个爱活动的人,是先生阻止了她才不去。又如朋友们请鲁迅先生吃饭,同时邀请了许,先生还是不带她出来。有一次我去面邀,先生同我一起出门,我要许同行,先生说她是看孩子的,不会社交,即可想见。(《黄源楼适夷通信集》,上册,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P23)
为什么鲁迅限制许广平的社交自由?是由于鲁迅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出于保护家人的考虑?显然,这样解释是不够的。一方面,鲁迅是一个主张妇女解放的启蒙者,其反封建的一面何其鲜明;另一方面,鲁迅在骨子里又存在着恪守传统的一面。把许广平定位为“看孩子的”,就是这种传统思想在作祟吧。看来,男权主义在鲁迅那里也是根深蒂固的。鲁迅默认了母亲为自己做主的婚姻,据当时婚礼的行郎之一周冠五的回忆,依旧俗“穿套袍褂,跪拜非常听话”;周作人也说鲁迅“头上没有辫子,怎么戴得红缨大帽,想当然只好戴上一条假辫吧?”鲁迅一直在有名无实的婚姻里度过了许多年。这样一个忍受传统的鲁迅,与那样一个金刚怒目、发出反封建呐喊的鲁迅,之间的差异之大,令人难以置信。我认为,朱先生这样的叙述裂隙,展示的是一个矛盾的鲁迅。而这样一个矛盾的鲁迅,确令鲁迅的形象变得有些血肉丰满起来。
鲁迅和周作人失和的原因,因为缺少确凿的史料,成为鲁迅传记写作中绕不过的一桩悬案。早在鲁迅去世后七年,即1943年,竹内好就提出这样的疑问:“他和周作人的所谓失和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么又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失和呢?”“他和周作人既共同著书,又不计在书上署谁的名,其关系之密切,远非世间一般兄弟可比,事情僵到死不可解,是否也有着远比普通的亲族情感更深的芥蒂呢?”竹内好排除了“私生活”的原因,揣测道:“倘说有什么失和契机的话,那么也远非没有可能是因为在对方身上只看到了自己的弱点。”(《近代的超克》,P43-44)竹内好对这一解释,也是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对兄弟失和的解释,几十年来可以说有几种版本,但是多属揣测和想象,较少确切的资料加以印证。朱先生多方引用可信的材料,认为兄弟失和的原因,与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长期患有“歇斯台里症”有直接关联。羽太信子癔病发作时胡言乱语,很可能是周作人听信了羽太信子的挑拨,下狠心与兄长绝交。严家炎先生认为,朱先生此章“尽释疑惑,可成定论”,我认为这样说还为时尚早。令人疑惑的是,周作人明知道羽太信子患有癔病为什么还那么相信她呢?这是最起码的常识。周作人就是这样没有理智吗?如果是他误解了鲁迅,为什么周作人在晚年写回忆鲁迅的文章时不作解释,避开此事呢?鲁迅早逝,高寿的周作人完全有机会和时间解开失和的死结,他却始终没有说明原由。这其中,或许会有更深的隐情吧。因此,兄弟失和的原因,将来还需要更有力的资料来加以解释。从另一个角度说,正是由于兄弟失和充满了谜团,才构成了鲁迅传记中最有魅力的关键点之一。兄弟失和关乎手足亲情,更关乎个人隐私。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也许这件家庭琐事永远没有确切的说法了,但我认为,从这个事件,我们不是更可以看到人性深处一些隐秘的东西,看到那些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丰盈的细节吗?人的内心光明与黑暗的冲突,人性的复杂,不是单纯用意识形态能够简化得了的。
可以看到,如果跳出将传记人物意识形态化的固定套路,对人物行为的动机则会有不同的解释。即以鲁迅弃医从文为例。一般都取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的说法,说是受到一次观看时事幻灯片的刺激。朱正先生认为,“当然不会是一个刺激和一时冲动的结果”,朱先生引用材料,详细叙述了鲁迅在日本几年间对文学的爱好,以及对国民性的思考,介绍了鲁迅从事文学活动的远因,幻灯片事件只不过是促使他作决定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这样的解释是客观的,有不少材料作支撑。而竹内好先生则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他认为“幻灯事件和立志从文并没有直接关系”,“他并不是抱着要靠文学来拯救同胞的精神贫困这种冠冕堂皇的愿望离开仙台的。我想,他恐怕是咀嚼着屈辱离开仙台的”。“幻灯事件和找茬事件有关,却和立志从文没有直接关系。我想,幻灯事件带给他的是和找茬事件相同的屈辱感。屈辱不是别的,正是他自身的屈辱。与其说是怜悯同胞,倒不如说是怜悯同胞之余才想到文学的,直到怜悯同胞成为连接着孤独的一座里程碑。”(《近代的超克》,P57)
可见,竹内好先生主要是从人物心理的角度,从鲁迅所受到的屈辱感入手来解释弃医从文的,而不是从预先设定鲁迅为了拯救愚弱的国民的灵魂这个“崇高”的目的来加以解释的。
朱正先生写过四次鲁迅的传记,这一次重新书写,与前几次的差异是明显的。朱正先生说:“我希望现在写的这一本能够保存下去。”这是一个传记写作者的自信,通读全书,我认为作者的这种自信并非虚妄,但是,也应该看到,在书中的鲁迅身上,依然存在着过分意识形态化的影子,离一个真实的鲁迅尚有一些距离。自然,这责任并不在朱先生,时代只是给我们的视野敞开这么多。未来,随着文化语境的变迁,肯定还会出现新的鲁迅传记的。
我常常想,我们的思想是不是过于明晰化了?我们对历史的解释、对历史人物的看法是不是过于本质化了?小而言之,我们对鲁迅的认识也太简单化了。鲁迅是很丰富的,任何把他简约化的企图都是对他的真实性的遮蔽。当竹内好先生在六十多年前说“鲁迅在本质上是一个矛盾”、“文学者鲁迅也是一个混沌”的时候,我认为倒是把握住了鲁迅的精髓。也许,于一片混沌处,一个真实的鲁迅会向我们洞开,走近真实的鲁迅,我们不需要一直带着那份清晰的路线图。
(本文编辑 钱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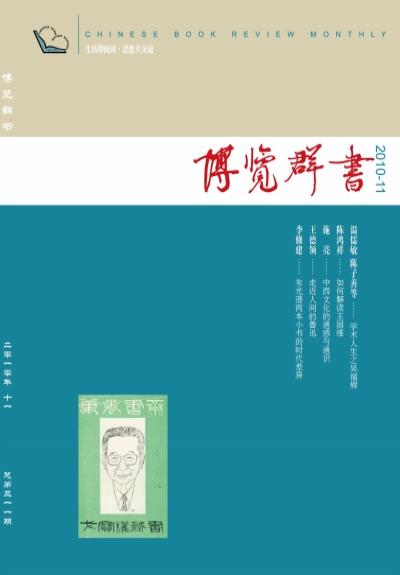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